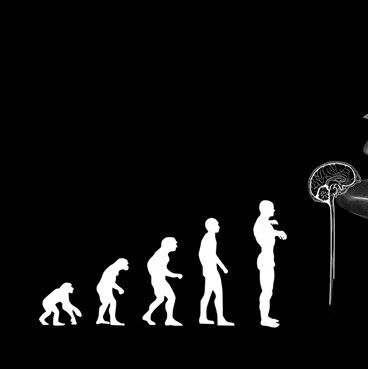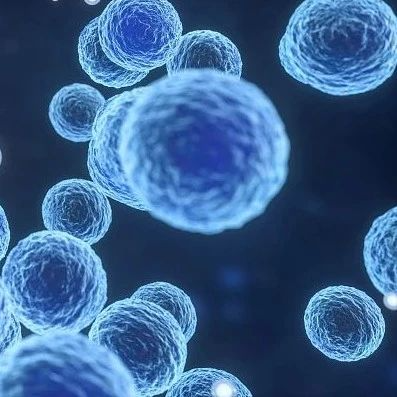比尔·盖茨下一次来北京的时候,面对他曾经捐助、握过手的艾滋病患者,和更多没有受益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艾滋病人群,他或许会感到成就和……失落。
一段缘分就此结束,很多颗心灵从此荒芜。2013年,盖茨基金会5000万美元援助中国的五年期项目正式到期了。中国卫生部-盖茨基金会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以下简称“中盖项目”)从2007年开始运作,五年来在推动中国的政府和民间组织NGO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方面,起到了不可代替的示范效应,但之后是否继续投入新的资金尚不确定。
今年4月8日,博鳌论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比尔·盖茨,对盖茨基金会同中方有关部门就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控烟、生物医药研制等合作表示赞赏,中方愿深化合作,共同致力于促进人类健康、消除贫困,使合作成果更多地惠及各国人民。
对于特殊而敏感的艾滋病世界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感慨的转折时刻。除了中盖项目,过去十年在中国扮演重要角色的全球基金项目(The Global Fund)、克林顿基金会艾滋病行动组织(CHAI)、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RCC)、中国-默沙东艾滋病合作项目(C MAP)等也都在2013年前后接近尾声。
这些国际基金会和跨国公司曾支付中国“抗艾”事业的花销一半以上,完成了阶段性的使命,在公众健康的历史上和相关人群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现在,中国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药品已经全部由中央财政支持。2012年,这笔支出为81348万元人民币,占抗艾总经费的59.36%。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把钱管好,而是把钱花好。”当我见到盖茨基金会中国办公室首席代表叶雷时,他正在没有椅子的办公桌前查阅邮件——节约、高效,这也是盖茨基金会的资金利用宗旨。叶雷说,前五年5000万美元项目结束以后,盖茨基金会还在筹措未来五年在中国的发展计划,“艾滋病仍在我们的关注领域内,总体支持、协助中国控制艾滋病这个大原则没有变,但应该不会有与以往规模相似的资金注入。”
盖茨曾经说,“从医学角度看,中国的艾滋病疫情同其他国家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真正意义非凡的是,在短短几年中,中国政府对HIV/AIDS的态度就从忽视转变成重视,并将其提上了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不过,为了取得成功,中国需要得到国际上的支持、鼓励和技术协助,因此我们决定要站出来提供自己的帮助。”
中国在抗艾方面已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今年5月19日,第30个国际艾滋病烛光纪念日,卫生部发布数据称,中国已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近50万例。近十年来,中国接受艾滋病抗病毒药品免费治疗的人数从零提升到现在超过20万人。2012年,中国有1亿多人进行了艾滋病病毒检查。
直到当了商业记者,我才意识到自己大学时当艾滋病志愿者的意义,也在无意中见证了中国艾滋病防治领域的一些重大变化。
2007年4月,盖茨第十次访华,到访卫生部和北京市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盖茨和防艾NGO志愿者、艾滋病感染者握手。当时,我在离疾控中心不远、位于陶然亭公园的北京市宣武区红十字会实习。对于一个担任学校红十字会会长、业余时间在大学生中传播性健康及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大三女生来说,盖茨基金会进入中国是一件大事。没想过三个月后,我跟中盖项目成了邻居。
那年夏天,我走过两条街,转到宣武区南纬路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性艾中心”)实习,先是到“中国全球基金第五轮艾滋病项目”做了三个月。办公室在附近一个宾馆的三楼,同一楼层还入驻了中盖项目、中英艾滋病策略支持项目等。项目混杂,偶有外国人士进出,有时我也加入他们的餐后聊天,想象在联合国工作可能也不过如此。
在另一条街道的京纬宾馆,有美国疾控中心(CDC)、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全球基金第三轮、中美项目等。中国第一个大型的政府与企业合作的艾滋病防治项目——中国-默沙东项目在旁边的一个小区里办公。这些国际合作项目由境外基金会或企业与卫生部合作,在性艾中心体系中建立执行办公室,即项目办。
我对全球基金并不陌生,其他几个学校的红十字会申请过他们的资金。全球基金2003年进入中国,截至2013年已有六轮,分别是第三至六轮、第八轮以及RCC项目,是投资最多的国际合作项目。其中,第五轮项目针对性工作者、男男性接触者和流动人群。因为这段实习经历,我的法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题目为“为什么男性同性恋是预防艾滋病的目标人群之一”。
第五轮项目当时的主管萧燕把我领进办公室。房间里容纳五人工位,已经有三位项目官和一位项目助理。如果说以前我在红十字会的第N级分支是负责“花钱的”,现在则变成了“发钱的”。全球基金第五轮项目要在2006年至2011年投入近3000万美元,通过以控制性传播为主的综合干预措施,遏制艾滋病在黑龙江、吉林、辽宁、重庆等七个省市的高危和脆弱人群中蔓延。承接机构包括地方疾控中心及很多性工作者、男性同性恋发起的NGO。
时隔五年后,我又回到陶然亭公园和天坛之间的这个艾滋病防治集中地。我没有找到原来的同事——这是意料中的事情,在艾滋病的世界,生命旦夕祸福。疾控中心已于2012年6月迁至北京昌平区小汤山新址,当初那些项目后来都搬到京纬宾馆办公,先后到期之后,现在只有全球基金第八轮、中盖项目、中国-默沙东项目等还留在这儿做收尾工作。楼道空荡,脚步声寂寥回响。
我在第五轮项目实习时的同事们都已经解散了。主管萧燕辞去了性艾中心的体制内工作,去了一家跨国公司。以前的项目官,有两个回了家乡的疾控部门;另一个出国留学几年,回来在性艾中心做了科室主任。和我关系最好的项目助理,现在在一家丹麦化学品公司做中国总裁助理。
还留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几乎所有项目在2012年底接近到期。这意味着中央财政将需要接手原本支持1/3至1/2的中国抗艾经费。而在此之前,它们就经历了好几次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让一些项目资金缩水很多,全球基金又因对资金的规范性审查在2011年冻结了对华抗艾援助。
我的QQ中几个社区小组负责人的头像再也没亮起来。重庆一个志愿者QQ签名改成:“我还在,你们呢?”一位NGO负责人说,这些国际项目到期其实是第二轮“大浪淘沙”。
中国第一次艾滋病疫情在2003年发布,结果令人惊讶:中国或存有84万艾滋病病人和病毒感染者。
性艾中心政策研究与信息室主任吕繁对那次疫情普查和分析印象深刻。他强调,“那是在世界卫生组织、美国CDC等国际机构的帮助下完成的”。他记得,当时疫情有几大特点,其中三项极为突出:一是全国低流行、局部高流行;二是2003年的发病率、死亡率集中爆发;三是血液传播(包括吸毒、卖血等)为主要途径。这几点在河南、安徽等地表现明显。
已经证实艾滋病病毒传染途径主要有三种: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人体感染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后,艾滋病(AIDS,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一般会在7-10年内发病,如果没有及时接受抗病毒治疗,脆弱的免疫系统甚至难挡正常的感冒。
2004年,华裔导演杨紫烨拍完姚明、约翰逊参演的艾滋病公益广告后,去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拍摄几名艾滋病孤儿的生活,《颍州的孩子》获2006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看到孩子在田野、坟地奔跑玩耍,观众无不动容。
这些艾滋病孤儿面临两大困境:生活和治疗。我曾经在河南遇到一个我见过的年龄最小的艾滋病感染者。2007年夏天,我跟随北京红十字会工作队去河南,我们要离开一个公立孤儿院的时候,一个6岁的小姑娘突然扑上来,抱住一位医生的腿,“叔叔,带我走!”在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之前她从不说话,我们以为她是哑巴。
小花的父母因为卖血感染病毒,在她不足3岁时去世。她原本跟着奶奶生活,还没过4岁就成了真正的孤儿。小花的叔叔因为她的病,不愿接管她,任她在老人的土房子里自生自灭。村里人知道她得了“坏病”,偶尔送给她一些吃的。最后,来自外界的援助将她安顿到公立孤儿院。她的病情终于恶化。我们见到她的时候,她因为肺部感染,有些发烧。医生说,需要尽快安排她到北京接受治疗,像这样病情的患儿一般撑不过8岁。临行前,一位负责人蹲下来承诺,再过一个星期,就来接她去北京。于是就发生了以上令人心酸的一幕。
回到北京后,小花被安排在北京佑安医院。半个月后,我和另一个志愿者去看她。小花一直盯着志愿者双肩背包上挂的玩具小熊。她画了一幅画,上面有花朵、房子和背书包的孩子。小花说,一周后是她的生日,那时她就可以上学了。
两周后(中间有事耽搁,没能给小花过上生日是我最后悔的事),我和那个志愿者带着蛋糕、玩具熊和书包,病房里却是空的。我们刚想去找重症监护室——那是我能想象的最差情况,在门口遇到了护士长。
“小花走了。”
“哪儿去了?”
“在她生日前一天,并发感染……”
我从来没那么难过过。那个玩具熊和书包在我办公室里放了很久。后来我去媒体跑石油、钢铁等神经粗砾的能源行业,远离让人心痛脆弱的艾滋病领域,或许是一种逃避。一位NGO志愿者跟我说过,艾滋病只会损伤两样东西:免疫系统和信心。
一度严峻的艾滋病疫情,在国际上引起很多担忧和争议。2003年,中国政府宣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84万,发病人数为8万,已跃居亚洲第二,仅次于印度。世界银行报告称,如果处理不当,艾滋病会在三代人的时间里毁掉一个社会。“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在自己的国家不让这个问题溜走的人。”2003年11月,克林顿在清华大学参加“AIDS与SARS国际研讨会”时说。“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当选央视“感动中国”2003年年度人物。
2003年,河南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免费检测、治疗、遗孤免费入学等救助措施。时任省委书记的李克强,以政府拨款建设市级血站等手段,尝试控制污血源头。当年叶雷在美国CDC工作,有一次到河南调研,在午餐会上与李克强讨论过遏制当地艾滋病疫情的话题。叶雷对河南控制“源头”的思路和铁腕执行很赞赏,“那套方案不是国际建议的,是李克强自己想出来的。而且他不是搞卫生工作的人,他是搞经济的。”
河南等地的试点工作颇有效果。2006年初,国务院以此为纲,签发了《艾滋病防治条例》,将保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接受免费检测、免费治疗、母婴病毒阻断、遗孤入学以及相关生活救助等政策制度化、法律化。
在救助进步和政策明确之后,境外基金会在中国防艾领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更多国际项目涌入,很多NGO在2007年前后忙碌起来。
2007年8月,全球基金第五轮项目在呼和浩特组织了一次培训,学员是来自各地的共15个以男性同性恋为目标人群的NGO小组。当时中国已经有至少两万人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但男性同性恋是其中重要的人群之一。他们自发形成的NGO,能起到预防和干预艾滋病的作用。所以我们设置专门课程,培训他们有关项目、管理、财务等各项能力。
这时候,李想的名字又反复出现在我的任务栏里。他2002年4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支持小组“红树林”。这在那个年代并不多,他们有相关的NGO经验,就成了我们培训的常客,经常被我的约请电话骚扰。
李想出生于吉林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大二献血前做血检,查出他1993年因血友病胃出血,接受治疗输血时感染艾滋病病毒,至今已20年。“那时候我们对于艾滋病只知道一点,就是会死。再多一点,就是会死得很难看。”每个认识或听说过李想的人都会在潜意识里把他作为一种生命奇迹。他的手机一直保持开机,接电话时他会问,“你好吗?”
培训第二天晚上,李想才来。当天他在云南参加另一场培训。他穿着一件黑色长风衣,跟我寒暄几句,张开双臂,“我不会介意如果你介意我。”第二天,他突然内出血,我们不得不从北京空运药品给他治疗。我在房间陪他输液至深夜。“我希望能看到明天的太阳。”他说,“这是我每天都要许的愿望。”
从呼和浩特回来不久,我去过李想在佑安医院附近的办公室。墙上贴着各种规章制度、防治知识。旁边还有励志名言和李想自己写的小随笔(他读的是中文系,有作家梦)。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主要是接听感染者的相关咨询来电。
2013年3月,我再次联系李想,他的办公室已经没了,“红树林”自2009年以后不再承接新项目。那年他母亲过世,李想因培训在外忙碌,没赶上最后一面。“很后悔。我可以像个英雄一样努力做NGO,比较贫困地去献身奉献,却忘了要像平凡人一样生活。”
我们约在一个咖啡馆,一见面,他又给了我一个拥抱。他的身体状况比以前好多了,面色有些红润。原来他用的药品来自国外机构捐赠,批次不同且经常断药,使他病情始终不稳定。2006年国内普及抗病毒治疗之后,他可以定期定量地得到药品。他最大的一个变化是结婚生子了。这对艾滋病患者极其不易,只有将体内的病毒载量控制到极低水平,不具传染性,才能正常生育。
李想给我看了一张照片,他妻子抱着1岁半的儿子在甜蜜微笑。李想已不需要为抗病毒药品奔波,只需定期到医院领取即可。他过上了正常人的日子,手机保持开机,万一还有感染者向他打电话咨询呢?即使没事,打个电话知道他好好活着,也是一种安慰啊。
艾滋病的阴霾虽然没能消散,但毕竟已经向普通疾病转变,患者不再那么讳疾忌医。抗艾也发展成了一个产业,但是商业力量所起的作用却不大。
2007年9月,从呼和浩特回来不久,经主管萧燕介绍,我转到性艾中心的治疗与关怀室实习。旁听了一些关于艾滋病的会议,我基本了解了当时中国抗艾的矛盾所在——药品供给问题和NGO的身份问题:即资金和药品从何而来,官方还是境外基金会;又向何而去,什么样的NGO是真正需要的。
叶雷后来告诉我,抗艾国际合作项目在中国大抵分为两类:一类是“计划经济”,一类是“市场经济”。可归为后者的只有盖茨基金会。“计划经济”模式是指草根NGO只需对周期内的工作内容作出承诺,如完成多少次高危人群行为干预,或是举办多少次宣传活动,对结果不做考量。多数NGO都会承接这类国际合作项目,有点像吃“大锅饭”。
盖茨基金会的“市场经济”则采取“计件计酬”,结果导向。它拿出5000万美元中的2000万美元,由中国卫生部下属的两个国家级NGO组织(性病艾滋病协会、中国预防医学会)牵头,在全国15个省市挑选一批草根NGO。后者针对同性恋、吸毒者和性工作者这三个目标人群,寻找艾滋病高危人群去卫生部指定的地点做HIV检测、服务、咨询和行为干预。工作效果以检测人数判定,比如每检测一例艾滋病血样可得62元报酬,每发现一例阳性可得300元。
“盖茨基金会为所有对艾滋病有需求的人服务的话,再多的钱也不够用。”叶雷说,“我们的创新就在于把政府和NGO结合起来,用经济刺激的方式,使抗艾工作逐渐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模式。就像催化剂一样,同样一笔钱用得好可以建立一种长久、持续的机制,国家可能就有比我们多几倍的钱投入进来。”
不过在药品发放问题上,境外基金会和跨国药企都谈不上什么创新。中国从2003年推广艾滋病抗病毒免费药品治疗,国内药厂(如东北制药集团)在这一年才具备仿制相关药品的能力。但直至2009年,中国的抗艾用药基本由艾滋病抗病毒主要用药拉米夫定(Lamivudine)的专利持有者葛兰素史克捐赠。而全球基金、克林顿基金会、中英项目等同时补充。
2004年7月,葛兰素史克与中国卫生部签订备忘录,捐赠18万盒和32万盒两批益平维(每片含200毫克拉米夫定的药剂名为益平维,1995年被批准用于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而每片含100毫克拉米夫定的药剂名为贺普丁,被广泛用于治疗慢性乙肝)。但该合作对新增病例估计过低,按照约定,第二批32万盒益平维应该在2009年第一季度末捐赠到位。但截至2008年4月,中国累计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人数即已达44629人。药品供给不足问题愈发棘手。
在性艾中心治疗与关怀室实习没多久,该室的抗病毒药品负责人休产假,我便暂时接替她的工作,在每季度的最后一个月与全国各地负责人核实下一季度的艾滋病抗病毒药品用量并协调发药。
2008年3月的一天,我在学校有课,却被一个电话召回性艾中心。电话从河南一个市打来,当地药品负责人的声音急促而恐惧:“你们赶紧调配药品吧,这边病人要割腕血洒县政府了。”这种紧急情况并不少见。我把应对此类需求的文件放在办公室桌面,这是固定格式,每次“报警”响起,我只需要填上时间、地区和数量即可发送给相关部门。
我记得,性艾中心多次上书卫生部督促葛兰素史克提前履行药品捐赠,同时摸索建立药品需求预测系统。当时克林顿基金会以艾滋病儿童治疗为例,建立了一套小型预测系统,对性艾中心颇具借鉴意义。领导们四处开会,以期解决供求困境。当时的困难在于:官方担心批准强行仿制抗艾药品引发国际纠纷,国内药企执行强仿其实是“赔本赚吆喝”,葛兰素史克只按备忘录行事……
到2008年6月我结束实习时,他们为2009年以后的药品来源找到了一个好途径——招标采购。但再过两年,这也不是问题了。中国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药品已经全部由中央财政买单。性艾中心治疗与关怀室主任张福杰原来最头疼怎么才能让更多病人接受抗病毒治疗,现在不愁药品来源了,他又有新的烦恼:抗病毒药品延长了很多艾滋病患者的生命,却可能让他们死于肝硬化(艾滋病与丙型肝炎在主要传播途径上存在重合,在全世界两者并发概率颇高)。
这次重回性艾中心,我有个遗憾,没能找到曾经使用的那台电脑看一看。当年负责发放药品时我被告诫严密保管存储数据的U盘:一经丢失,责任重大。我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得知,2008年初,中国大陆已有33028人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那曾经是抗艾领域的“最高机密”。如果放到现在,作为一个商业记者,我的第一反应会是: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市场啊……
当然,艾滋病防治就像长征,需要漫长的奋斗过程和复杂的体系建设。除了国家层面的因素和人们观念的更新之外,成百上千的NGO组织和志愿者以及资助他们的各类国际基金会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2012年10月,一名25岁的天津男孩因感染艾滋病病毒而被医院拒绝实施肺癌治疗手术,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天津“海河之星”艾滋病感染者关爱小组负责人李虎站出来呼吁后,男孩得到了医治。11月26日,在世界艾滋病日到来前夕,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克强在北京与防治艾滋病民间组织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座谈,李虎受邀参加。
李克强在跟NGO座谈时说,对于有成功、丰富经验的民间防艾组织,一定不能让他们“断炊”,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等办法,来弥补他们的资金困境,这比单一让CDC或公立医院花钱更有效率。他甚至直接提出建议,国务院防艾委要立即着手研究,成立中国自己直接支持社会组织的防艾基金。
李虎在2006年被查出感染病毒之前,拥有一家人力中介公司。他2007年开始自己垫资做防艾工作,保障艾滋病人的权益,让他们能够享受公正的待遇——这已经是常识,与艾滋病患者握手、共同进餐等一般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病毒,他们在社会上不应该受到歧视。在天津一栋民宅里,“海河之星”有6名工作人员,接待前来咨询的HIV携带者和高危人群,帮助他们消除“自我歧视”。
被副总理接见,李虎觉得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虽然这坚定了很多抗艾工作者的信心。李虎正在创建一个维权网站,希望吸引更多律师像帮助农民工一样帮助艾滋病患者。那些国际项目的到期,使一些NGO萌生退意,李虎很坚定,“也许我会开一个餐馆,厨师、服务员都是感染者,你会来吗?”
国际合作项目的减少会对中国抗艾产生多大影响?性艾中心政策研究与信息室主任吕繁说,“局部影响肯定有,比如原来支持社会组织的钱怎么办,国家就得考虑怎么来补缺……长远影响还不好说,从国家财力和领导人表态来说,经费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近几年,中国抗艾事业有进步,卫生部或性艾中心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NGO组织,双方达成一种供求关系,形成良性循环。这不能不归因于那些国际项目给予的项目推动和创新启发。
无国界医生“病者有其药”项目负责人陈又丁,原来供职于克林顿基金会抗艾药品项目。“国际机构都在撤,这些资金也在撤走,但是中国的国际合作不能撤。国际项目最为重要的其实不是那点资金,他们带进来的技术、管理、理念的价值远远大于钱。”
盖茨基金会在全球树立了公益样本。有一次,比尔·盖茨的孩子们(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问他,为什么不帮助纪录片里那个瘸腿的非洲小男孩。盖茨夫人梅琳达说:“我们努力帮助很多和他一样的孩子。”盖茨解释说:“我们做的是批发,不是零售。”
过去十年,全球基金、盖茨基金会等国际项目在中国抗艾领域既做了零售,也做了批发;既输入了资金,也输入了理念。我还记得,2007年我作为一个实习生进入艾滋病防治世界。那一年,比尔·盖茨在辍学创业32年后,回到母校哈佛大学获得荣誉学位。盖茨在演讲时说,“无论是通过民主制度、强大的公共教育、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或者广泛的经济机会,消除不平等才是人类的最大成就。”因为这句话,我会一直感激这段实习生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