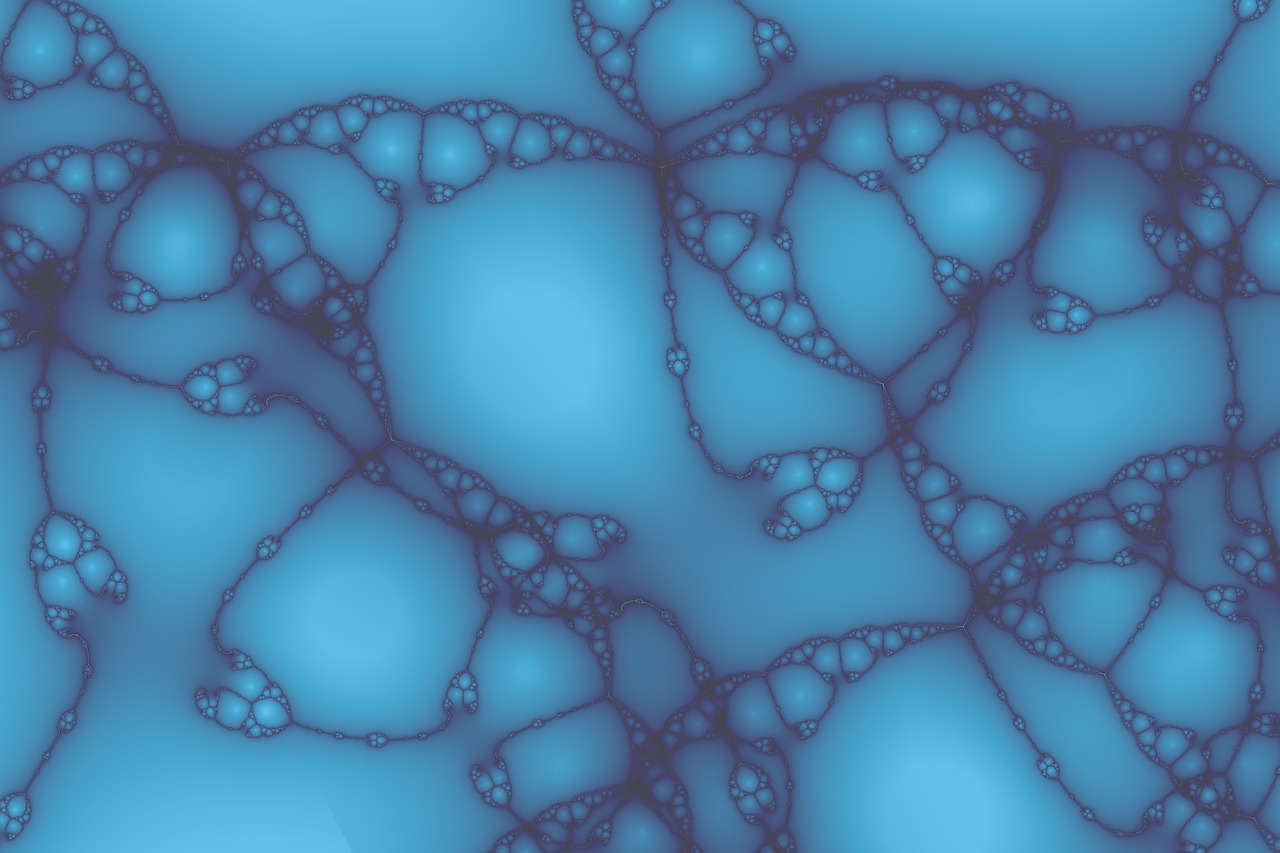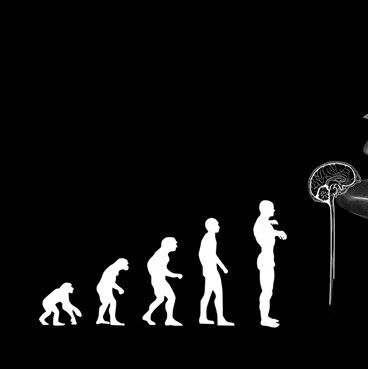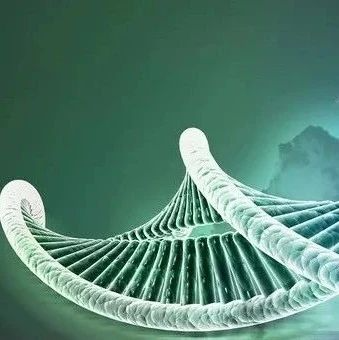不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冷战对抗时期,少数不可一世的国家出于种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曾进行过一些泯灭人性的所谓“科学”实验。它们往往以邻为壑,肆无忌惮地将弱小邻国的土地甚至这些国家的人体作为实验室和试验品,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有些实验的真实详情数十年后才得以真相大白,有些直至当下仍不能还原历史。但是这些实验的毁灭性后果却长久而深深地折磨甚至威胁着这些国家的人民。
健康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诉求之一,除力免战火外,从现在起,国际社会应努力杜绝某些国家打着科学的幌子从事不人道、泯灭人性的所谓“科学”实验。
冷战时期 美国:拿危地马拉囚犯做性病实验致1300多人感染
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2011年8月29日公布初步报告说,上世纪40年代,美国研究人员在明知违反伦理标准的情况下,故意使危地马拉1300多名囚犯和精神病患者感染上梅毒等性病。实验过程中,83名人类“实验小白鼠”死亡。

美国媒体2011年2月曾披露,半个多世纪前,美国政府在国内也曾以研发药物和研究治疗方法的名义,对疾病患者及囚犯开展人体实验。类似实验在美国国内曾进行40余次。
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认为,正如美国国内曾发生过的情形一样,这项得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并没有把危地马拉人当做人对待,甚至没有告诉研究对象他们在开展研究。
委员会说,两年多的实验过程中,1300多名危地马拉人染上淋病和梅毒等性病。尽管对梅毒等性传病的研究是当时一项重要科学目标,但没有任何理由通过上述方式进行,这项实验展示了“系统性失败”。
委员会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埃米·古特曼说,一些知情者妄图隐瞒事实,因为他们担心一旦事泄自己会成为公众批评的目标。
危地马拉秘密人体实验事件由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医学史学家苏珊·里维尔比首先揭开。这位医学史学家在梳理已故医生约翰·卡特勒的资料时发现,1946至1948年间,卡特勒在危地马拉的监狱里展开了一项秘密人体实验,美国医疗人员在受害者不知情或者未经受害者允许的情况下故意让当地人感染上淋病和梅毒。实验对象随后接受青霉素治疗,以测试青霉素是否能治愈或预防梅毒。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10月就这一事件向危地马拉道歉,并要求成立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进行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预计将于12月公布。而危地马拉总统当时称该实验为“违背人性的犯罪”。
危地马拉秘密人体实验事件唤起美国人一段可怕记忆,即“塔斯基吉梅毒研究”。自1932年起,美国卫生部门官员在亚拉巴马州以免费治疗梅毒为名,召集约600名黑人男子作为实验品,秘密研究梅毒对人体危害。该研究直到1972年被媒体曝光才终止。当事人被隐瞒长达40年,大批受害人及其亲属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
美国政府官员2010年10月承认,类似实验在美国国内曾发生十余起。不过,美国媒体查阅医学杂志文章和剪报资料后认定,涉及美国公民的研究实验数量超过40起,主要进行于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这些实验项目包括在康涅狄格州使精神病患者感染肝炎病毒、在马里兰州让囚犯吸入流感病毒、在纽约市一家医院向慢性病患者注射癌细胞等等,其中一些实验只是为满足好奇心,没有取得实际成果。
根据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2011年8月29日公布的初步报告,为了测试青霉素能否治愈和预防性病,美国研究人员竟然在1946年至1948年故意让1300多名危地马拉囚犯、精神病患者和性工作者染上淋病、梅毒和软性下疳等性病,其中只有大约700人得到某种治疗。截至1953年底,共有83名实验对象死亡。

这一令人发指的丑闻最初曝光于2010年秋天。在阅读已故医生约翰·卡特勒留下的档案文件时,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从事女性和医学史研究的专家苏珊·里维尔比惊讶地发现,卡特勒曾于上世纪40年代在危地马拉的监狱里秘密进行人体实验。里维尔比说,在得知这一惊天秘闻后,自己“差点儿从椅子上掉下来”,怎么也无法相信会有这种事。
在一篇长达29页的文章中,里维尔比披露说,美国实验人员有时让囚犯、妓女或精神病患者喝下含有性病病毒的蒸馏水;有时为了让一些妇女感染性病,拿带有病毒的注射器划破她们的口、脸和手臂……而这些“人类小白鼠”对实验目的毫不知情。这些实验对象有的接受了青霉素治疗,有的则没有接受过任何治疗。
事情被曝光后,危地马拉政府立即予以强烈谴责。危地马拉总统阿尔瓦罗·科洛姆称之为“违反人性的罪行”。危政府表示,“保留将这一事件提交国际法庭的权利”。危地马拉副总统埃斯帕达29日称,危地马拉方面已经找到5名非法实验的幸存者,并准备把他们送到危地马拉最大的医院进行检查,以确定实验对他们本人和家人所造成的影响。据介绍,这5名幸存者年龄在85岁左右。埃斯帕达表示,危地马拉政府将对检查结果进行分析,然后决定如何应对。检查结果将于2011年10月由科洛姆提名组成的总统调查委员会公布。
2010年10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被迫就此事向科洛姆表示道歉,强调这种行为“违反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并下令组成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对事件展开深入调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也联合发表了道歉声明。
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表示,这项得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项目,“没有将危地马拉人当人来看待”。虽然对梅毒、淋病等性病治疗方法的研究是当时的一项重要科研目标,但研究人员没有任何理由在明知违反伦理道德的情况下进行这种实验。该委员会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埃米·古特曼谴责“这是医学史上可耻的一页”。她说:“参与实验的研究人员连对人权最低限度的尊重都没有,实验毫无道德可言。”据报道,这个委员会将在2011年12月发布最终调查报告,“评估该事件涉及的道德问题”,以“确保类似事件今后不再发生”。
2010年10月,曾有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类似实验不止在国外进行,在美国国内也发生过“10多次”。美国媒体2011年2月爆料说,上世纪40至60年代,美国政府曾打着“研究治疗方法和研发新型药物”的旗号,对国内的囚犯和疾病患者进行了“高达40多次”人体实验,包括让精神病患者感染肝炎病毒、让囚犯感染流感病毒以及向慢性病患者注射癌细胞等。更令人愤慨的是,一些实验仅仅出于研究人员的好奇,根本没有任何成果可言。
事实上,在美国开展人体实验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媒体早在1972年就曾披露,从1932年开始,美国卫生部门官员在亚拉巴马州征召了大约600名黑人,秘密开展梅毒对人体危害的研究。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这些被无辜剥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竟然一直被蒙在鼓里。
二战期间日本:731部队拿6000多中国人做细菌实验
侵华日军731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高统治者下令组建的细菌战秘密部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研究中心。他们利用健康活人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等实验,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
731部队1932年在中国哈尔滨设立研究中心。这支部队拥有3000多名细菌专家和研究人员,分工负责实验和生产细菌武器,残忍地对各国抗日志士和中国平民的健康人体用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和毒气进行活人实验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先后有一万多名中、苏、朝、蒙战俘和健康平民惨死在这里。
经研究证实,这个部队当时已具有可将人类毁灭数次的细菌武器生产能力,他们的“研究成果”投放战场,致使20万人死伤。1945年8月,731部队为了销毁罪证,在败退时炸毁了这里的主要实验设施。
2000年,有关专家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并公布了731部队用活人作细菌实验的原始文字材料“特别输送档案”,是该部队败退时来不及销毁而意外留下的,是侵华日军进行人体实验的直接罪证。
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了若干支细菌战部队,共设有63个支队,而731部队是他们的研究和指挥中心。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不仅在731部队进行,其他各细菌部队包括部分日军陆军医院都干着同样的人体实验的勾当。到1943年末,侵华日军几乎每个师团都配有防疫给水部队,以防疫给水为名进行各种人体实验活动。
此次公布的人体冻伤实验就是由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完成的,该部又称北京1855部队。据这个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翻译官、已去世的韩国人崔享振证实:“这支部队每年至少要用500人进行人体实验。”
另据原广州8604部队队员丸山茂提供,在日军侵占香港期间,大量香港难民涌入广州,广州8604部队利用难民营中缺少食品为由,向难民提供掺入细菌的食品,致使数百人死亡。
二战结束前,日军为消灭罪证炸毁了731细菌战实验基地的大部分设施,并将实验资料移交美军,后被用于朝鲜和越南战场,对战后西方细菌战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731部队的大部分战犯至今未能受到应有的审判。
为永久保存侵华日军731部队遗址这个二战中极为特殊的标志性遗址,从2000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有关部门耗资近亿元对731部队遗址进行了首次全面清理,发现了300多件人体解剖用具。同时,采取措施对这个遗址进行保护,决定将其建成一座呼唤人类和平的遗址公园,并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学者近日宣布,日军侵华时期,被日本宪兵队以“特别移送”方式交给关东军第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受害者中,已有1467人的身份得到确认。据专家估算,这个被日本侵略者称作“马路大”的群体,至少在6000人以上。

所谓“马路大”,在日语中意为“圆木”,是731部队对那些接受人体实验的受害者的污辱性称呼。在这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部队的特设监狱里,他们一律无名无姓而只有编号,像动物一样被强制接受各种细菌或毒气的折磨,或被活活冻死,最终毁尸灭迹,无一生还。
翻开历史档案,你会发现,他们在跨进那道地狱之门前,其实都曾生动地活过、笑过、抗争过、战斗过。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为抗日奔走。
战后的60多年里,为还原那段历史,许多人仍在艰难前行。
在他去世将近70年之后,已经很难有人说得清楚,朱云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给亲友留下了腼腆如大姑娘的印象;在日本宪兵队拍摄的照片上,身陷绝境的他身姿挺拔,目光炯炯;宪兵队长对他的评价却是:“性格狡猾,生来懒惰,为了生活不择手段。”
2010年4月,他的名字和照片被制成黑底白字的牌位,贴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纪念长廊上,旁边是比他年长两岁的哥哥朱云彤。他们的身份,都是死于731部队人体实验的“马路大”。
据东安宪兵分队审讯记录记载,朱云岫曾在密山县黄泥河子恒山煤矿做机电工。1940年8月,朱云岫与苏联谍报员万信相识并被发展为谍报员。9月27日,朱云岫与万信一起越境入苏,在“浦拉特诺夫卡”国境警备队接受指令:调查平阳镇兵力、兵种和兵营数量以及鸡西发电厂的施工进展情况,获酬金120元。
审讯记录称,朱云岫在收集上述情报时患病,卧床两个多月,没能按规定日期入苏,预感到可能惹怒苏方,会有生命危险。为安全起见,便策划以加入日满军警密探为名开始谍报活动。
同属这一谍报网的,还有朱云岫的哥哥朱云彤和工友王振达。朱云彤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密山县国境警察本队警长。1940年9月至12月间,朱云彤曾3次越境入苏,接受的任务指令为:调查二人班、半截河和平阳镇附近日军情况,特别是飞机场的状况,并调查密山县公路网及铁路状况,共计获酬金330元。
1941年2月,万信被捕,但他当时并未供出几名下线。
二战期间德国:“改良人种”实验造成40万人死亡
约瑟夫·门格尔曾是纳粹德国设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希特勒冲锋队军医,绰号“死亡天使”,其任务是尽可能多地“消灭”不能劳动的囚犯,用活人做“改良人种”试验,先后有约40万人惨死在他手下。
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德国情报机构驻意大利的头目瓦尔特·拉乌夫精心策划名为“老鼠路线”的纳粹战犯逃亡计划,将一些纳粹分子分别送到西班牙、埃及、黎巴嫩和阿根廷等国,门格尔就这样逃脱了历史审判。
在门格尔的亡命岁月中,他的一个名叫沃尔夫冈·格哈德的奥地利朋友扮演了重要角色。此人把自己的名字供门格尔在巴西使用,还把自己在巴西东南部一家造纸厂中技术主管的工作留给门格尔。依靠这些伪装,门格尔从人间“蒸发”。
翻阅门格尔留下的所有文献,对于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犯下的罪行,门格尔没有丝毫忏悔。只是在1976年的日记中,描写做细菌试验的时候,他提到了“痛苦的放弃”字眼。
国际社会始终没有放弃对门格尔的追踪,在维也纳专门成立了搜捕门格尔的犹太人组织。其间,曾有人到阿根廷翻阅门格尔的档案,发现门格尔曾在阿根廷首都郊区的圣伊西德罗区住过10年。据说阿根廷警方曾逮捕过一个被认为是门格尔的人,但由于德国政府未向阿根廷提供证明其身份的指纹,只好将他释放。
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次出现门格尔已经死亡的报道,但其准确性都无法保证。直到1985年,在巴西圣保罗附近埃姆布的一个公墓,人们发现了据称是门格尔的遗骸。经过国际法医病理专家小组检验后,证实遗骨确属门格尔,并确定其为溺水死亡,死亡时间是1979年。
门格尔死亡的消息传出后,搜捕门格尔的犹太人组织把为捉拿门格尔而募集的100万马克赏金捐赠给了150位曾被门格尔当作试验品而幸存下来的受害者。
德国东部城镇韦尼格罗德2006年11月4日见证了一次特别聚会,约40名参与者都是德国纳粹秘密计划的受害者。他们被称为“希特勒婴儿”,是当年德国纳粹为实现人种净化、制造“雅利安超人”秘密计划的产物。
这是“希特勒婴儿”首次公开聚会。如今都已年过六旬的“希特勒婴儿”们在聚会中公开讲述各自的故事,向世人揭露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2006年11月4日,在德国东部韦尼格罗德,一名因纳粹的“生命之源”计划而出生的男子在拍照。当天,40名被称为“希特勒婴儿”的德国纳粹秘密计划受害者在这里举行公开聚会。他们是德国纳粹为实现人种净化而制定的“生命之源”计划的产物。许多“希特勒婴儿”被迫与亲生父母分离,在纳粹党徒家中长大。他们往往缺乏正常关爱,同时还有很强烈的负罪感,饱受心灵创伤。 新华社/路透
“希特勒婴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纳粹秘密计划的受害者。当时,德国纳粹为实现雅利安人对世界的统治,在残忍屠杀数百万犹太人和被纳粹归为“劣等”族群的同时,还炮制了一个名为“生命之源”的秘密计划。
秘密计划由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牵头,目的是在全欧范围制造“优等”雅利安人。纳粹在欧洲建立特殊产房,符合种族标准的女性可以在此生产金发碧眼的未来精英。其中约60%产妇为未婚妇女。纳粹利用当时社会不接受未婚先孕的现实,将新生儿从母亲手中夺走,送到纳粹党徒家中抚养。
以1940年为例。纳粹占领德国周边一些国家后,鼓励士兵在当地寻找雅利安血统的妇女,并在这些国家建立10所特殊产房。最后约有8000名婴儿出生。
两年后,即1942年,纳粹开始在这些国家仔细挑选具有雅利安人特征、金发碧眼儿童,并把他们强行带回德国,接受纳粹教育,使之“德国化”。
为掩盖事实,纳粹在二战结束前销毁“生命之源”计划的许多文件。欧洲到底有多少“希特勒婴儿”至今仍是未知数。据估计,仅在德国一地,这一数字就在5500人以上。
由于许多“希特勒婴儿”在纳粹党徒家中长大,或父亲就是党卫军成员,他们有很强的负罪感,许多人不肯公开自己的身份。“希特勒婴儿”们4年前才开始首次私下聚会,2005年正式成立了“生命痕迹”组织。约60名组织成员中,大部分都是“希特勒婴儿”。
“生命痕迹”举办这次公开聚会,鼓励“希特勒婴儿”正视历史、讲述自己的故事、互相鼓励支持,并分享寻找亲人的经验。
组织成员维奥莱特·瓦伦博恩说:“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要鼓起勇气公开身份,讲述我们的故事。”
另一名成员吉塞拉·海登赖希表示,有必要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述这段历史故事。“如今孩子们知道很多历史事实,他们的历史知识很丰富,但他们对历史缺乏情感上的联系,”海登赖希说:"希特勒婴儿"的故事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是关于母亲、父亲和孩子的故事。这能帮助学生们把历史和自己联系起来,更好地理解历史。”
2006年11月4日,40名被称为“希特勒婴儿”的德国纳粹秘密计划受害者在德国东部的韦尼格罗德举行公开聚会。他们是德国纳粹为实现人种净化而制定的“生命之源”计划的产物。许多“希特勒婴儿”被迫与亲生父母分离,在纳粹党徒家中长大。他们往往缺乏正常关爱,同时还有很强烈的负罪感,饱受心灵创伤。这张摄于11月5日的照片是当年在韦尼格罗德修建的一所医院,不少“希特勒婴儿”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新华社/路透
纳粹的秘密计划造成“希特勒婴儿”被迫与亲生父母分离,遭受许多创伤。
弗尔克·海尼克现年66岁,是纳粹1942年强行带到德国的“希特勒婴儿”之一。当时只有两岁的海尼克因为具有雅利安人金发碧眼的特征,被纳粹从乌克兰送到德国莱比锡,由一对富人夫妇养大。他至今不知道亲生父母的身份,这一事实困扰他大半生。
尽管和其他一些“希特勒婴儿”相比,海尼克的生活还算不错,但他说:“我心中总有遗憾。那是一种没有父母,没有根的感觉。”他从2005年开始着手寻找自己的亲人。
现年64岁的汉斯-乌尔里希·韦施是出生在韦尼格罗德的“希特勒婴儿”,被送到前民主德国长大。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一直阻止他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几年前,韦施终于找到自己的母亲。“我和妈妈心灵相通,”韦施说:“当她见到我的时候,她高兴极了。这些年她也受了很多苦。”
和许多“希特勒婴儿”一样,韦施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关爱,所以总感觉自己被所有人抛弃。他说,那是一种“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恐惧”。
除遭到社会歧视与遗忘外,许多“希特勒婴儿”从小接受纳粹教条“洗脑”,因而受教育程度不高、情感不健全。在挪威,不少“希特勒婴儿”仍在通过法庭争取他们在战后遭受耻辱与忽视的赔偿。
生物探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