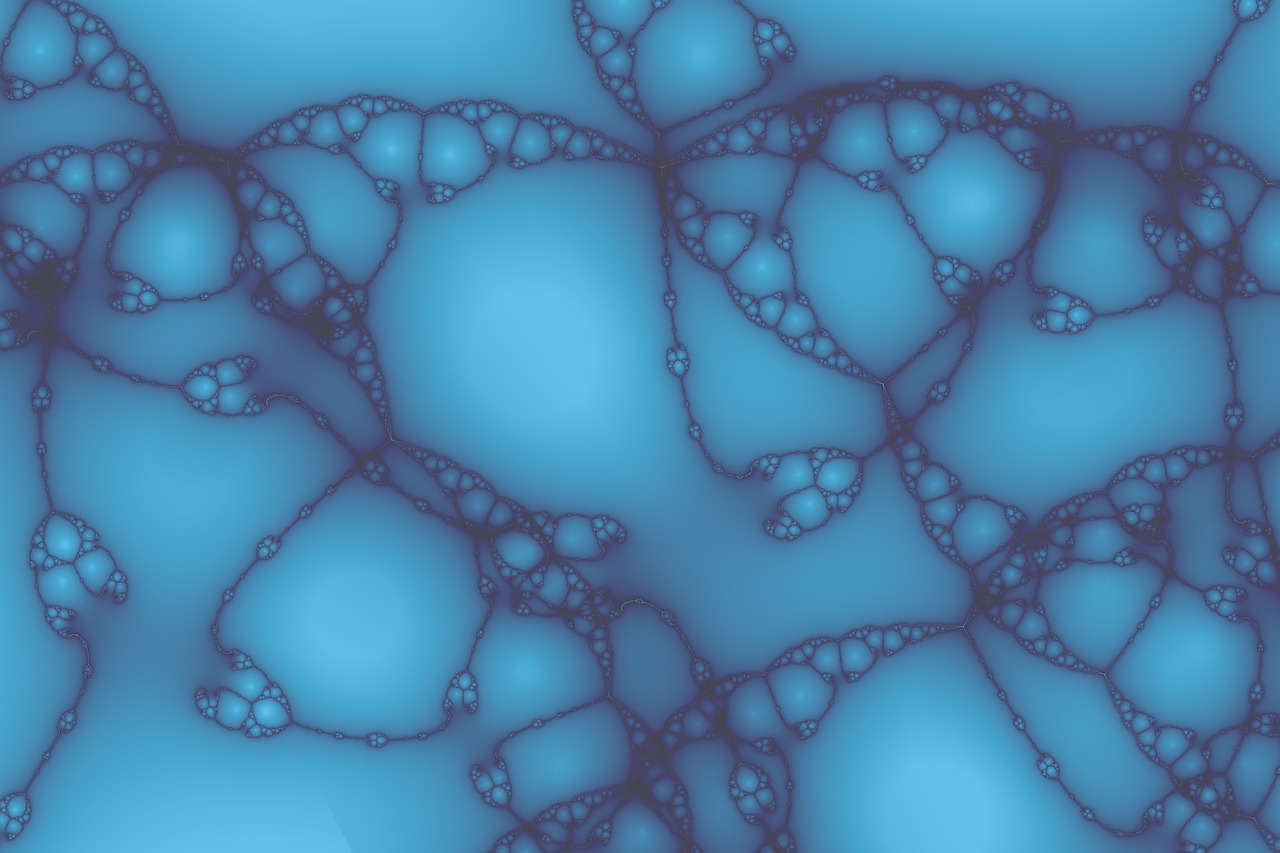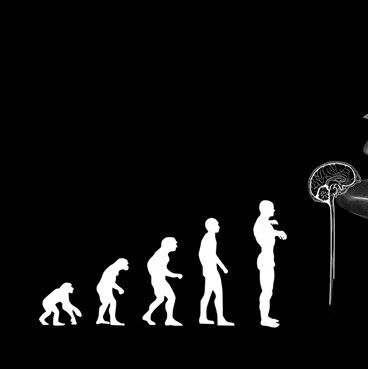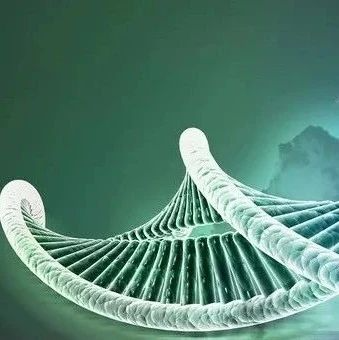癌症细胞的阿基里斯之踵
李福洋
一、希腊神话故事: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
阿基里斯(也有翻译为“阿喀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他的母亲是女神忒提斯。为了让儿子能够长生不死,女神忒提斯将出生不久的阿基里斯浸入冥河进行洗礼,阿基里斯从此刀枪不入,百毒不侵。然而,由于冥河水流湍急,母亲还得捏着他的脚后跟,不敢松手,以至于独独剩下脚后跟未能浸入冥河,因此脚踵就成为他最脆弱的地方。后来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历时十年,其中阿基里斯一直是希腊人最勇敢的将领,只身一人挑战特洛伊主将赫克托耳,并将其杀死,还拖尸示威。这可惹怒了太阳神阿波罗,就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在阿波罗的指点下,赫克托耳的弟弟帕里斯(以射暗箭闻名,这场战争就是由他而起),抓住了阿基里斯的弱点,一箭射中他的脚踵,从而轻易地杀死了伟大的英雄阿基里斯,也使得特洛伊战争的黯然结束,双方两败俱伤,没有真正的赢家。“阿基里斯之踵”后来被喻为:无论再强大、再完美的人或事都有其弱点。
二、人类与癌症的战争,癌症化学治疗的难题
癌症就像一个强大的魔鬼,人类在与它的搏斗中,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目前人类暂时还处于下风。
化疗是治疗恶性肿瘤的重要手段。与传统的细胞毒性化学药物不同的是,基于靶标的分子设计与筛选是目前开发抗肿瘤药物主要策略。怎么理解靶标呢?如果把化学药物比作箭,那么传统的癌症化疗像是“乱箭穿身”,而现在要求的是要“一箭穿心”,这里的“心”就是化学药物准确识别、干预,并能专门致癌症于死地的关键分子,也称为癌症的“靶标”,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对正常组织的误伤,也称“副作用”。
然而,如何实现化疗药物在有效杀伤癌症细胞的药效范围内,对正常细胞和组织不产生损害,一直是现代抗肿瘤药物开发研究中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众所周知的难题。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其实就是缺乏真正意义上肿瘤特异性的靶标。
我们和肿瘤细胞不是简单两军对垒的关系,肿瘤常常是混在无辜群众中狡猾的恐怖分子,它们往往也有很强的“群众基础”,要想把他们和正常细胞区分开,既能有效杀伤肿瘤细胞,又不误伤正常细胞,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什么癌症(或肿瘤)这么难缠?
三、癌症的复杂性与靶标选择的困难
肿瘤的发生是遗传信息和表观遗传信息发生结构或功能上的变异累积的结果,是多步骤的发生过程。癌基因的激活和抑癌基因的失活,使得细胞逐步演化获得了一些共同的特性,如无限增殖能力、对增殖抑制和凋亡信号的耐受以及从周围环境获得各种支持信号的能力,甚至是逃避机体免疫的能力等[1]。一些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如PI3K,Ras,p53,PTEN, Rb, p16INK4a等在许多肿瘤细胞都频繁地发生突变,被认为是肿瘤基因中的“主角”。
癌基因被认为是癌症发生中的“趋动性因素”,当前抗肿瘤药物靶标的选择,主要是针对这些癌基因的产物。最成功的例子是针对Bcr-abl癌基因的抑制剂Gleevec(治疗白血病。Bcr和Abl是两个原本在两条染色体上互不相干的正常基因,由于染色体断裂时接错了,就被连接形成一个新的融合基因Bcr-abl,这个基因就成了导致白血病发生的癌基因。这个癌基因十分独特,在正常细胞是不存在的,因此针对它的抑制剂对相对应的癌细胞发挥杀伤作用的同时,对正常细胞的副作用就很小。然而,这种靠两种基因融合形成新的癌基因的情形在人体其它癌症中并不多见,因此它的成功难以复制。
其它的癌基因怎么样呢?大多数癌基因是由于过度表达或点突变引起的活性的增强,在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都存在和发挥作用,只是在量多或量少的区别,因此针对这些癌基因很难避免对正常细胞的伤害。
有些癌基因,直接抑制或纠正其异常功能状态极其困难,比如癌基因如Ras。正常Ras的活性是一过性的,但是由于突变就变成持续性的,也就成了癌基因了,就像肌肉运动,收缩与松弛转换很快是正常的,如果只是持续收缩,就变成抽筋了,那就不能行使正常的功能,反倒引起病理损害。Ras在很多癌症,尤其是肺癌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如果能纠正Ras的功能,那就可以治疗很多类型的癌症,但是实际上极其困难,很显然不能单纯抑制Ras的活性,可是要想纠正这一功能异常,那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目前没有那个实验室,也没有那个公司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化学药物抑制策略也无能为力,那就是癌症主要是由于抑癌基因突变失活引起。癌基因因为突变失活了,很难通过化学手段让它恢复活性,“起死回生”;有些突变让抑癌基因表达不全(半截)或不表达或稳定性降低,那化学抑制剂策略就更“找不着北”了。
有些问题太难解决,我们可以放置在一边,等待将来新的技术或方法出现再去解决,像数学上的许多“猜想”留给后人去解决;但是有些问题,尤其是和应用有密切联系的问题我们却等不得。然而,“寤寐思服”依然“求之不得”,怎么办?是否可以考虑绕道而行,是否可以考虑智取?
可是,癌症要比我们想象得还要来得复杂。
新一代测序技术的应用让肿瘤基因组的研究速度一日千里,海量信息让人目不暇接,甚至眼花缭乱。近年来肿瘤全基因组的大规模测序的结果揭示了肿瘤基因型的高度复杂性与出乎意料的不均一性[2]。除了上述的一些主角外,肿瘤还带有大量其它基因突变,虽然这些突变在各种肿瘤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仍然对肿瘤的发生发展有促进作用。据英国Sanger 肿瘤基因组中心Straton等预测,约20%的蛋白激酶会主动参与肿瘤发生发展(人基因组编码约700多个蛋白激酶)[3]。如果其它类型的基因也是按照类似的比例在肿瘤发生中起作用,那么这将构成一个巨大、复杂的基因网络。
面对高度复杂、变异多样的肿瘤基因网络,靶标的选择就变得极其困难,单纯瞄准几个癌蛋白似乎远远不够。问题好像显得越来越复杂,复杂得让人眼晕,令人望而生畏。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再强大的敌人也有弱点,再复杂严密的网络也会有漏洞。毛主席有句经典的话“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我们不能止于自信,还要积极认真思考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面对复杂难解的绳结,亚历山大大帝挥剑斩结,一剑定夺;面对面对高度复杂、变异多样的肿瘤基因网络,我们的拿什么去解决癌症药物靶标问题?
(亚历山大之剑:公元前233年冬天,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进兵亚细亚,一到弗尼吉亚城便马不停蹄率部径望朱庇特神庙奔去。原来该庙完好地保存着几百年前戈迪亚斯王系的一个复杂的绳结,谁能解开此结就能成为亚细亚王。但每年许多人试解此结均无功而返。一行面对此结也不知从何处着手,只见亚历山大拔出战剑,一剑把绳结劈成两半,难解之结就这样轻易解开了,亚历山大也当上了亚细亚王。)(注:这个故事可能会有多种解读,这里仅做隐喻,请勿延伸)
科学探索,观念先行。有些问题的解决要依赖技术,有些问题的解决则需要创造性的观念。
肿瘤合成致死基因概念,或许就是一把解开癌症这个高度纷繁复杂的“难解之结”的 “亚历山大之剑”。
四、什么是“合成致死”?
“合成致死”(synthetic lethal)最早是源于模式生物酵母研究中的遗传学概念,基因间功能性相互作用的一种形式;比如,A基因,和B基因,如果不同时发生突变,无论突变哪一个,对细胞的存活都没有影响;如果A和B基因同时突变则对细胞是致死性的,那A基因和B基因之间就是互为合成致死关系,也互为合成致死基因。
对遗传学不熟悉的朋友可能还会心存疑惑:“合成致死”中的“合成”究竟是什么意思?能有这样的疑问,说明你是个喜欢思考的人。我们这样考虑一下:如果两个基因同时突变了会致死,那么自然界你能目睹到这样事件自然发生吗?当然不会。因为这个生命(或许是一个个体,或许只是一个细胞)在形成之初就夭亡了,你连它的面都见不着,又怎么能目睹它的死亡? 所以在遗传学上,“致死”只能用这种类型个体在后代中能否出现来判断。打个比方,就像你的一位朋友,你天天在办公室见他,可是有一天开始,你再也没见到他,实际上他既没外出也没调动,哪儿都不会去,谁都没有再见过他,包括他的亲人;那他会去哪儿呢?只有一个地方:天堂(当然,你也可以说被外星人带走了^_^)。
对于外在原因导致的死亡,很容易观察,也很容易确定因果关系,但是对与内在原因导致的死亡却无法捕捉到,只能通过人工再现来确定因果关系。我们通常是人为地将两个基因同时突变,人工再现“死亡”,以验证我们的推测,所以就称为“合成致死”。
大家注意:1. 这种关系不是A基因和B基因之间孤立的相互作用关系,而是在这两个基因所在的基因组这个大背景下,它们在功能上的相互作用。2. 基因间的合成致死性提示这些基因之间在某些重要功能上的互补性,当细胞的某一个或一些基因突变导致细胞的某些功能异常时,细胞的存活依赖于另外一个或一些基因。
“合成致死”在低等模式生物是一种普遍的基因间相互作用方式。
在模式生物芽生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除了10%的关键基因(单基因缺失即可致死),其余约80%的基因都存在合成致死基因,而且大部分基因都和多个基因间存在合成致死关系[5]。例如,负责DNA复制的基因和DNA损伤修复基因就存在合成致死相互作用;负责细胞有丝分裂检查点的基因也和DNA修复基因存在合成致死相互作用。
Dixon等通过遗传学手段描绘了另一种模式生物-裂殖酵母(Saccharomyces pombe)的基因合成致死相互作用网络,并与芽生酵母进行了比较。这两种单细胞模式生物虽然在同属酵母,但在进化树上遗传上关系相距较较远,许多生物学特性也有很大区别,但是合成致死相互作用却有相当的保守性约(约占总基因的30%)。在模式生物线虫和果蝇都发现了一些与酵母保守的合成致死相互作用[6]。
当我们从低等模式生物借用这个概念来研究人类癌症的时候,我们最关心也是心里感到忐忑的问题是:这个概念是否适用人的细胞?人基因之间是否也存在这种“合成致死”关系?用专业的描述就是:合成致死性是不是一种普遍、保守的基因间功能相互作用模式?
可以说,这个问题暂时无解。
基于于人和酵母在多种基本生物学过程和以及基因组功能上的保守性,提示人的基因组也可能存在合成致死相互关系的网络。
这时候其实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的勇气和精神。
五、 肿瘤细胞的“阿基里斯之踵”-合成致死基因
大胆探索还是需要些信心的,让我们先从理论上寻找一些信心。
肿瘤细胞的一些恶性行为虽然给肿瘤带来应对进化压力选择的优越性,但是也给肿瘤细胞自身带来多重“危机” (stress)。例如肿瘤细胞,失去控制的DNA复制,给基因组的稳定性带来问题,DNA频频出错,损伤不断[7];肿瘤细胞快速无节制增殖、生长,蛋白合成和能量供应依赖性增加;由于肿瘤局部的缺氧性,使得肿瘤细胞对糖酵解的依赖增强[8, 9],非整倍体性带来细胞有丝分裂应激和蛋白毒性应激[10]。为了应付这些应激,一些对正常细胞而言并不重要的基因也被动员起来,应对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平时在幕后默默无闻的基因就成了肿瘤存活的关键的分子,而对正常细胞来说,却是冗余的,因此这些分子也就构成了肿瘤的“致命弱点”[11, 12],有可能成为肿瘤特异性的靶标。
具体到每一个肿瘤,由于其突变的癌基因或抑癌基因不同,其对应的致死基因也会有所不同,因此,肿瘤合成致死基因是肿瘤基因型(突变型)特异性的。理论上,肿瘤合成致死基因的鉴定将可以巧妙地解决前面叙述的难题。
① 肿瘤合成致死基因具有肿瘤基因型特异性,因此,以其为靶标将可以特异性地区分肿瘤与正常细胞;② 化学手段虽然无法恢复失活的抑癌基因,但可以干预其对应的合成致死基因,特异干预肿瘤恶性行为;③ 一些难以干预的突变癌蛋白如Ras,则可以通过干预其对应的合成致死基因迂回解决。
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时候极个别的成功往往会给整个领域或行业注入极大的信心,推动整个领域的发展。
如果以历史回顾(或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去分析目前热火的一个抗肿瘤药物Parp1抑制剂的阶段性成功的,我们就不难发现“合成致死”的影子。这个抑制剂用于治疗BRCA2突变的乳腺癌,效果极其特异,有效剂量和毒性剂量之间相差近百倍,这样它的副作用就很小,十分安全。为什么会这样?
乳腺癌基因BRCA2和单链DNA断裂修复基因PARP1之间就存在合成致死的关系。BRCA2是乳腺癌中最常见的发生突变失活的抑癌基因基因,Brca2蛋白主要负责DNA双链断裂的同源重组修复。细胞内总会有些内源性,如DNA氧化损伤,烷基化修饰,DNA合成中碱基错误掺入等,PARP1主要碱基切补修复(base excision repair,BER),在DNA复制过程中,单链断裂如果不能及时修复将会转变成双链断裂。正常情况下,两条通路共同协作,保证DNA被完整修复,但是在肿瘤,当BRCA2发生突变失活,细胞只剩下一条途径修复单链断裂,在加上肿瘤的异常增殖和DNA复制,以及氧化应激等,都给细胞带来更多的损伤负荷,细胞的存活就更加依赖于PARP1的修复功能。抑制PARP1的功能就可以选择性地杀伤BRCA2突变的乳腺癌细胞,而对正常细胞却没有影响。目前多个公司开发的Parp1抑制剂都已进入II期临床试验[13],《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就临床试验的阶段性结果破例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述评[14],标题为:抗肿瘤药物研发的新方向:合成致死。
如何去发现和鉴定合成致死基因呢?我随后另文介绍《开采肿瘤基因组的“金矿”》。
参考文献
1. Hahn WC and Weinberg RA, Rules for making human tumor cells. N Engl J Med, 2002. 347(20): p. 1593-603.
2. Hanahan D and Weinberg RA, Hallmarks of Cancer: The Next Generation. Cell, 2011, March 4. 144(5): p. 646-674.
3. Cancer-Genome-Atlas-Research-Network, Comprehensive genomic characterization defines human glioblastoma genes and core pathways. Nature, 2008. 455(7216): p. 1061-1068.
4. Greenman C, S.P., Smith R, et al, Stratton MR., Patterns of somatic mutation in human cancer genomes. Nature, 2007. 446(7132): p. 153-8.
5. Pan, X., et al., A DNA integrity network in the yeast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Cell, 2006. 124(5): p. 1069-81.
6. Tarailo M, T.S., Rose AM., Synthetic lethal interactions identify phenotypic "interologs" of the spindle assembly checkpoint components. Genetics, 2007. 177(4): p. 2525-30.
7. Braig, M., Lee, S. Loddenkemper, C. Rudolph, C., et al., Oncogene-induced senescence as an initial barrier in lymphoma development. Nature, 2005. 436(7051): p. 660-5.
8. Ducray, F., Y. Marie, and M. Sanson, IDH1 and IDH2 mutations in gliomas. N Engl J Med, 2009. 360(21): p. 2248; author reply 2249.
9. De Carli, E., X. Wang, and S. Puget, IDH1 and IDH2 mutations in gliomas. N Engl J Med, 2009. 360(21): p. 2248; author reply 2249.
10. Whitesell, L., Lindquist, S. L., HSP90 and the chaperoning of cancer. Nat Rev Cancer, 2005. 5(10): p. 761-72.
11. Luo J, S.N., Elledge SJ,, Principles of cancer therapy: oncogene and non-oncogene addiction. Cell, 2009. 136(5): p. 823-37.
12. Solimini NL, L.J., Elledge SJ., Non-oncogene addiction and the stress phenotype of cancer cells. Cell, 2007. 130(6): p. 986-8.
13. Fong PC, B.D., Yap TA, et, al., Inhibition of Poly(ADP-Ribose) Polymerase in Tumors from BRCA Mutation Carriers.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9. 361(2): p. 123-134.
14. Iglehart JD and Silver DP, Synthetic lethality--a new direction in cancer-drug development. N Engl J Med, 2009. 361(2): p. 18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