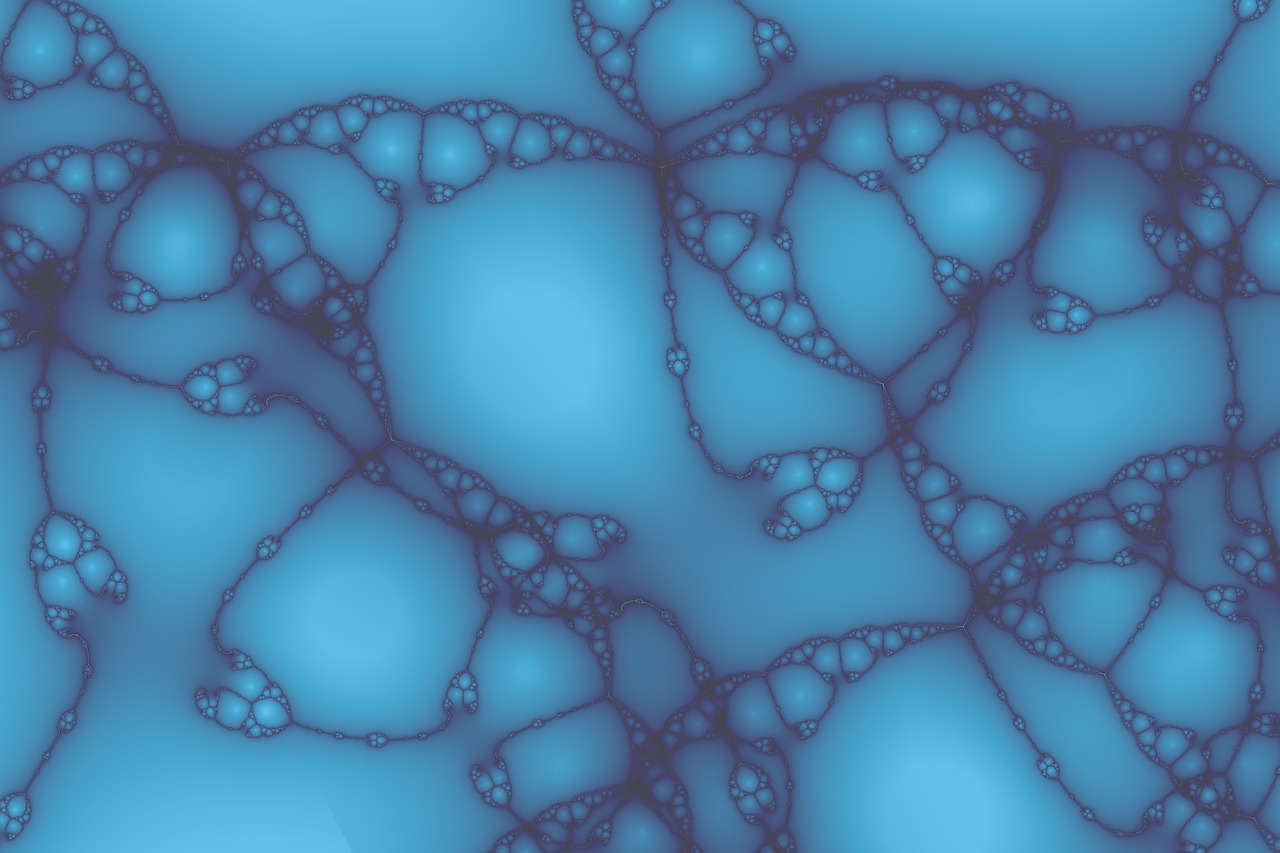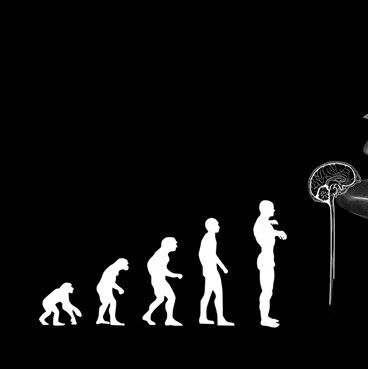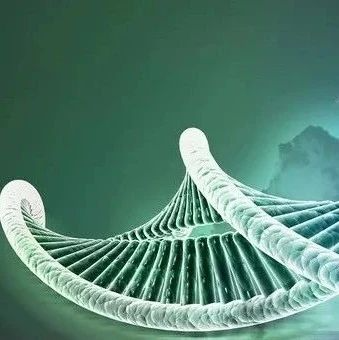1984年9月9日凌晨,一名陌生人从开着的客厅窗户走进了M女士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家中。发现M女士正在睡觉,便企图强奸她,但恰巧屋子里的其他人醒了,这个陌生人逃离了现场。M女士向警方描述了行凶者的特征:黑人,重约170磅,身高在5'7”到5'9”之间,小发辫,戴着蓝色棒球帽。
警察在她的住宅附近搜索,在离她房子一个街区的地方,发现一个大致符合描述的人站在他的车旁边。这个名叫Joseph Pacely的男子说,他的车坏了,想找人帮助他发动汽车。但是M女士认为他就是嫌疑人员,于是他被指控。
在Pacely审判几个月后,记忆研究员Elizabeth Loftus代表他作证。她告诉陪审团,记忆是不可靠的;压力和恐惧可能降低了M女士确定行凶者的能力以及人们辨认自己种族以外的人会存在困难。
Pacely被无罪释放。“这样的案件对我来说意味着更多东西,”Loftus说,“我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为无辜的人伸张正义的角色。”
职业生涯四十多年,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Loftus所做的证明记忆不可靠的实验比所有其他研究人员都多。她已经习惯了作为专家证人用她所学为数百刑事案件作证——告诉陪审团,记忆是脆弱的,目击者的描述与真实事件远非一回事。
她的工作为她赢得了一片喝彩,但也为她树敌不少。批评人士认为,在她热情的对记忆准确性提出挑战的同时,已经罪受害者造成了二度伤害,同时也是在帮助杀人犯和强奸犯。她曾经被起诉过,也被殴打过,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为了防身,她去射击场学习过射击,并且在办公室里还保留了几个用过的枪靶,那是她的骄傲。
现在,这位68岁的科学家开始为法律制度带来了持久的变化。去年7月,新泽西最高法院根据她的调查结果作出裁定——陪审员应该警惕记忆不可靠性和将目击者证词的作为标准程序的不完善性。Loftus正在与其他国家的法官合作,使这些变化涉及的地域更加广泛。
伦敦城市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Martin Conway认为:“现在美国正在发生的一切真的是一场革命” ,Loftus的工作对于塑造这些变化“极为重要”。

可锻铸的回忆
Loftus说,她开始涉及心理学之初,这门学科是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作为一个刚从斯坦福大学数学心理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她对这一门科学并不感冒:“我总是坐在研讨会的后面,非常无聊,给我的叔叔写信或者把裙边卷来卷去。”
最终,一门社会心理学课激起了她的兴趣,她开始研究词语如何被大脑定义并记忆。不过,还是好像缺了点什么。“有一天,我正在和我的一个表弟吃午饭,我告诉她关于我们近期的伟大发现——人们给‘一只鸟,黄色(a bird that's yellow)’命名比‘一只黄色的鸟(a yellow bird)’更快。”表弟不为所动,开玩笑说他们在浪费浪费纳税人的钱。“这时候,我决定,我想要的是有更多实际应用价值的东西。”
Loftus寻找一个有意义的方法来研究记忆并获得资金。当时一个在美国运输部工作的前斯坦福大学的工程师说,他的雇主可能会投资研究车祸。
在这个指引下,1974年Loftus提议研究交通事故的目击者,从而获得了一笔资金。她很快就发表了几个有影响力的研究结果,揭示目击者证词的局限性。她向人们展示车祸的影片剪辑,并要求他们估计汽车的速度。他发现提问时采用的措辞,对于人们估计的速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问题是“汽车相互碰撞时的速度有多快?”回答者通常给予更高的速度估计。而被告知是“汽车挨到一起”的人给出的估计速度较低。
被问及“两车撞击”的人在事故发生一周后,有两倍以上的几率表示自己看到了碎玻璃,即使视频中并不存在破碎的玻璃。Loftus说:“我意识到,这些提问传达了一些信息,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污染记忆的过程,我们把它叫做误传效应。”
随后,她继续发表了几项研究报告,显示记忆如何被扭曲,目击者确定犯罪嫌疑人照片的能力也是不可靠的。目击者可能会听到的任何说明,都有对他们辨认和判断的能力存在潜在影响。
Loftus急切的希望把这些研究结果放到现实生活中来,并开始涉足法律案件获得一些证人。她的第一个案子——一名女子被控杀害了虐待她的男友——焦点在于她是正当防卫还是谋杀。目击者对于女子拿起枪到开枪之间的时间间隔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几秒,有人说是几分钟。Loftus质疑证人的记忆,女子被无罪释放。
Loftus连同她的研究一起,于1974在Psychology Today magazine上发表了文章。“那篇文章出来后,律师希望我能协助他们的工作,法律专业人士希望我来开办讲座。”
她的一些试验非常高调——包括被称为山腰绞杀手的连环凶杀案和1992年警察被指控殴打建筑工人Rodney King。她甚至参与了一个法律系学生Ted Bundy的案件,这名学生被指控于1974年绑架一名女子。Bundy被定罪,只能逃跑。1978年再次被捕后,他最终承认杀害了30人。
帮助有罪的人并没有给Loftus带来困扰:“还没有人因为我的证词被无罪释放后继续进行可怕的犯罪,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这会很可怕,但我只负责一宗法庭案件的一小部分。” 她也能从中获得报酬,500美元/小时。
杜克大学法学院的生物伦理学家Nita Farahany说,Loftus在法庭上的工作并不特别,代表不受欢迎的被告作证非常重要。“这表明,她一直试图做到真正的公正,她的目标是尽量提供准确的科学依据,不管涉及到谁。”
尽管如此,Loftus已经划分出了一个界限,例如John Demjanjuk,他198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以色列操作在集中营的毒气室。Loftus是犹太人,为了不给家人和朋友带来困扰,她拒绝作证。这种情况导致一些人指责她有双重标准。
深挖过去
1990年,Loftus接到了来自加州的辩护律师George Franklin的电话,他的女儿声称,在治疗过程中她恢复了几十年前他谋杀自己朋友Susan Nason的记忆。Loftus决定为辩护团队提供支持:“我认为这是相当可疑的,于是开始查找文献。” 她发现,几乎没有令人信服的研究支持这一想法,创伤性的记忆可能会被压抑多年。
尽管有Loftus的证词,Franklin还是被定罪,在监狱里,他花了五年之前,上诉法院审查,他女儿的陈述遭到质疑。
法庭上在恢复童年记忆而引发的案件激增,这助长了一些书籍的畅销以及高调的指控。 Loftus开始怀疑是否有可能制造复杂的、可信的回忆。“我想看看是否可以植入一个虚构事件的丰富记忆,” 她说。
Loftus与一个学生Jacqueline Pickrell一同进行研究,他们招募了24个志愿者,与他们的家人合作进行测试。他们给被测试人提供了童年期间的四个事件列表,其中有三件事是却是发生过的,第四件事——在商场走失——经参与者的亲属证实完全是Loftus编造的。四分之一的参与者声称他们记得自己曾在商场走失过。
战场
Loftus相信善意的心理治疗可能会在无意中将虚假的记忆植入到患者的头脑,她的证词导致了坚信患者在恢复失去的记忆的治疗师和对此持有怀疑的研究人员之间的一道鸿沟。为了解决这些“记忆之战”,美国心理协会(APA)委托专家对这个问题做一个报告,包括Loftus和其他三位临床心理学家。
由于报告团体意见不一致,最终出现了各自独立的报告。“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曾与Loftus一同参加报告的 康奈尔大学发展心理学家Stephen Ceci回忆道。
现在又方法让真实事件的创伤记忆在埋没多年后被记起,但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法院无法区分正确的或者是虚假的记忆。因此,一些童年虐待的索赔因为Loftus的证词不成立,这也是许多人敌视她的原因。
布朗大学的政治学家Ross Cheit于1995年开始恢复记忆的项目,现在有超过100个证实病例恢复记忆在他的网站上(https://blogs.brown.edu/recoveredmemory)。“Loftus总是在失败的一方,有时候她错的惊人,”Cheit说。他补充说,她的证词是对受害者心理上的伤害。“如果你告诉别人你认为他们的记忆是假的,而他们可以出示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所说为真,这多么讽刺。”
Loftus不相信Cheit网站真正恢复了记忆。她说“我因为不想伤害受害者就畏缩,那么当一个无辜的人被指控,他就成了新的受害者。一个无辜的人被定罪而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这更可怕。”
但她的证词和调查使她的专业人际关系变得紧张。接近1995年底,两名妇女提出正式投诉Loftus与APA。Lynn Crooks和Jennifer Hoult赢得了涉及儿童性虐待记忆恢复的民事诉讼案件,并且都指责Loftus歪曲事实。Loftus从APA辞职,有评论家推测她早就听到了风声,在被调查之前就离开了。但Loftus表示她的辞职是因为政治分歧,对于当时的控诉,她毫不知情。
1997年,Loftus和几个同事开始挖掘一个已公布的案例研究,在这个案件中,某某恢复了压抑的童年虐待记忆。他们发现她提供的信息非常可疑,可是先于他们研究结果的公布,某某已经联系了Loftus工作的华盛顿大学,指责Loftus的团队侵犯了她的隐私。大学没收了Loftus的文件,对她考察了近两年,不允许她发表文章。但最终该作品于2002年发表。随后的一年,某某起诉Loftus和她的合作者欺诈、侵犯隐私、诽谤、对她造成情绪困扰。那个时候正值Loftus刚搬到尔湾加州大学,案子在2007年尘埃落定,加州最高法院驳回所有诉讼,但Loftus 支付了7,500美元作为公害结算。
她的工作正在推动法律制度上广泛的变化。Loftus最近一直在与宾夕法尼亚州主审法官Jeannine Turgeon制定一套新规则。他们指示陪审员记忆“不是视频记录”, 要求他们在办案时考虑更多的因素。Loftus希望走得更远。法律程序的每一个阶段——从识别犯罪嫌疑人和讯问目击者——都有可能出错,“我想看到这样的事情正在实施,并不断教育人们记忆如何运作。” Loftus说。
心灵控制
与此同时,她的研究也转向了新的有争议的水上环境。考虑到在船上可以制造回忆,她一直致力于使用这些记忆来修改行为。“我们已经证明,你可以向儿童灌输吃某种食物会生病的记忆”她说,“我们也可以让人们在喝伏特加酒后感觉自己身体不适,以至于他们今后不想再喝这种酒。” 没有证据表明这会成功地从实验室转移到现实世界。即使这样做,这将违反治疗师的行为准则,并且可能会产生无法预见的后果。
“欺骗孩子让我不舒服,”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Judy Illes说,“为什么不能用积极的方式改变他们的行为,而不是使用诡计?”但是Loftus驳斥了这种担忧,她表示即使治疗师不愿这样做,孩子的父母也未必不想这么做。“父母对总是在对孩子说谎,例如圣诞老人和仙女。你原意拥有一个不健康的孩子,还是仅仅有一些虚假记忆的健康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