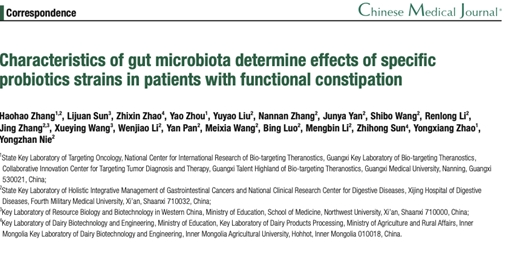在英国每年有2000人选择接受捐赠精子、卵子或者胚胎,20年以来通过这种方式出生的小孩已经有44000个。当发现自己是接受捐赠精子长大的孩子,你会有什么感觉?
米德尔塞克大学健康心理学教授Olga van den Akker去年写了一篇论文说到,那些通过接受捐赠精子出生的孩子成年后渴望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和兄弟,这不仅仅是一种好奇,他们把它当成了一种“根本任务”。
Akker教授说那些发现自己通过非传统途径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很难接受他们对自己起源的未知。英国有些女性说这个发现打乱了她们的生活。
Joanna Rose的故事:突如其来的消息——我不是你爸爸
Joanna Rose,44岁,英国人,是一名博士,目前和其两个小孩住在德文郡。Joanna的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血液学顾问。八岁那年,Joanna发现她爸爸在客厅哭泣。Joanna对此感到惊讶和不解,于是立马上前给予爸爸深切的关心以及深情的拥抱,并询问她爸爸出了什么事情。她爸爸告诉她关于捐赠的概念并说“我不是你的亲生爸爸”。当时Joanna 难以接受这个消息。
Joanna回忆说,“不考虑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很在乎我爸爸的感受,当时我抹去他的眼泪,安慰他说他是我唯一的爸爸”。
但Joanna爸爸当时的哭泣行为对她有深远的影响,并引起Joanna情绪波动。Joanna很感激自己有一个富裕的家庭,但她发现自己的感情开始撕裂,她很好奇谁提供了她另外一半DNA。
Joanna Rose的故事:情感态度和心理的转变
Joanna长得有5英尺10英寸高,和她现在的父母都不像。Joanna回忆,曾经有个商人来拜访她们家,问Joanna是不是遗传了爸爸的身高。Joanna当时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未见过他”。这样的回答使***妈感到非常的震惊。
Joanna的行为也解释了她父亲对她的态度。她父亲对他时而热情,时而冷落。然而,有时候她觉得如果她表现出对亲生父亲的好奇,就会被视为“不忠”。
当Joanna一个人的时候,她会站在镜子前,试图通过自己的脸看到她生父的脸。Joanna说,“我对自己长得不像我家里人感到深深的悲伤,也感到很失望”。
为了逃避压力和理解自己身份创造空间,19岁的时候Joanna搬到了澳大利亚。然而,多年后一些困难伴随而来,她患上了周期性抑郁症,在青年时期,她曾患有暴食症,且越来越想知道她到底是谁。
在Joanna十几岁的时候,她养父和妈妈就离异了,但是她一直和她的“爸爸”保持联系,一直到他去年离开人世。
接受捐赠精子这个事实使Joanna与她母亲的关系有点紧张,但这不影响她对妈妈的爱。Joanna对妈妈的爱对她周期性抑郁症的治愈起到一定的帮助。
Joanna最终感觉自己可以和妈妈公开的谈论自己的感受。Joanna妈妈说,当时接受捐赠精子的行为似乎是完全正确的,但她现在感觉这是一个很自私的决定。
Joanna Rose的故事:寻找生物学父亲
父亲的那次哭泣使30年来Joanna对自己另一边家族的未知感到失落。“折磨我的是关于另外一部分家族病史和种族的未知。我父亲是犹太人,而我只知道我另一半DNA捐赠者没有,关于他的一切我都不知道” Joanna说,“当你对自己一半基因起源一无所知的时候,你对自己是谁来自哪里无骄傲可言”。
Joanna对捐赠的伦理问题很关心,且她的博士研究课题与这些问题有关。但周围的人却认为Joanna应该知足。Joann说,她被告知如果没有捐赠精子,她就不会再这里,所有她必须认同这个事实。当Joanna和别人谈论自己的感想时,别人就会说“难道你宁愿自己没有出生?”Joanna感觉自己好像没有权利询问一样。
Joanna一直在搜集和自己出生有关的信息。但后来精子银行告诉她关于她的捐赠记录已被摧毁。如今很难找到关于Joanna另一半基因来源的数据,因为在1971年,这些事情都是秘密进行的,诊所建议父母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他们的后代)关于捐赠者的任何信息。
通过努力,2002年Joanna获得了高等法院批准的人权测试,同时高等法院立法禁止匿名捐赠。这意味着后续的人工授精生育的记录必须集中管理并保证其安全性。多亏了Joanna的努力,让其他接受捐赠精子出生的孩子们有机会了解他们另一半基因的来源。
这几十年,Joanna试图从母亲的言语以及行为中找到些线索。后来她发现她养父一直是不孕的,但是***妈一直渴望要孩子,于是***妈决定从哈利街诊所接受了捐赠精子来受孕。哈利街诊所的精子捐赠者大多数都是学医的学生,他们每捐一次可获£35的存款。
2004年英国成立了接受捐赠登记机构,捐赠者和捐赠者后代可将其DNA提交到该数据库可有望找到匹配的基因。Joanna在接受捐赠登记机构里面进行登记,根据当时哈利街诊所统计,她可能有300多个堂表兄弟姐妹,Joanna说这是个有趣又可怕的事实。
15年前她被告知有一个人可能是她另一半基因来源的捐赠者,这燃起了她的希望。Joanna试图与其取得联系,希望能找到她的病史和民族,但是法律禁止她与他联系,这让Joanna感到悲伤和沮丧,她将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是谁。
Christine Whipp的故事:一封揭示身世的信件
Christine Whipp,60岁,英国人,现和其丈夫(退休电子工程师)两个女儿和七个孙子住在德文郡。Christine说她母亲多年来多次提到“家庭秘密”,她说她会在死后的遗言里面透漏这个“家庭秘密”。
Christine说:“30岁的时候我和我妈妈的关系开始变得疏远,她60岁的时候我丈夫建议不再去看望她,因为她对我的批判态度和行为达到了情感虐待的程度。在她70岁生日的时候我送了她一张卡片,并附上纸条询问关于秘密的事情,并答应永远不再打扰她。”
Christine母亲及时给她回了信,告诉她,她的父亲由于儿童腮腺炎和严重的糖尿病而不育,在Christine6岁的时候她爸爸因为炎症发作而死亡。Christine的另一半基因来源于艾克赛特的一个生育诊所的捐赠精子。
Christine Whipp的故事:身世揭示后的情感态度
Christine回忆道,“自己对于这些令人震惊的消息毫无准备。尽管在孩童时代我有怀疑过自己的身份,但是从来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知道这个消息,世界好像停止了转动,我不得不重新阅读母亲前几次的来信。从表面上看,我似乎还是同一个人。然而,在这几分钟我的一切都变了。”
“当你晚年时发现自己是一个“捐助孩子”时,那种愤怒和背叛的感觉会很严重” Christine Whipp说,“我感到很生气,关于自己的身世我被骗了这么多年。未经咨询我就被剥夺了与自己亲生父亲联系的权利。不过,我总觉得我母亲憎恨我,这感觉就像拼图中的重要一块,对我来说意义是很大的。”为了证明这一点,Christine说她母亲在她10岁的时候再婚了,有了另外一个女儿,且对她宠爱有加。
收到这封改变人生的信件后,Christine没有进一步接触她母亲。但不可避免的是,一旦愤怒开始消退,泪水就开始流淌。在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接受捐赠怀孕,Christine有种被隔离的感觉。Christine 说,“我还有一个担心,我不知道自己另一部分家族病史,我对自己和我孩子的疾病一无所知。整个糟糕的情况让我感觉自己完全被放错了地方。我很沮丧,我很想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自己到底是谁?”
Christine Whipp的故事:寻找生物学父亲
Christine寻求其生物根源持续了九年。“当我发现我没有法律权利知道自己父亲是谁的时候,而且接受捐赠诊所没有关于我另一半基因来源的记录,我崩溃了。” Christine愤怒地说。因为在当时,妇科医生死后私人诊所的记录可能会被摧毁,且当时政府也没有相关记录,50年前也没有相关法律规定。
在诊所工作人员和捐赠者的帮助下,Christine最终联系到了帮***妈接受捐赠精子的医生家属。该医生的儿子在一次会议上注意到了一个DNA测试结果与Christine有家族类似性。后来证明她和他有生物血缘关系。自那以后他们保持联系,至今保存着独特的关系。
Christine的同父异母兄弟,在公立学校上学,在一个有仆人、有网球场和有船的家庭生长,而Christine,却生长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Christine生长的地方没有热自来水且只能去室外上厕所。
然而Christine抱怨的不是痛苦,她抱怨的是那些生育行业创始人没有考虑创造生育随后带来的身份危机。
Christine希望不曾知道这个消息,她说要接受这样的事实还需要很长的时间。Christine说,“血缘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像我一样通过接受捐赠精子出生的孩子即使有幸重返遗传根,也经常有被脱离的感觉。我希望人们打消接受捐赠受孕的想法。我认为这是自私而残酷的行为,它剥夺了孩子获取自然遗产的权利。”
Emma Cresswell的故事:一名年轻女子的态度
Emma Cresswell,27岁,是一名护士,有两个双胞胎哥哥。19岁的时候Emma知道自己是通过接受捐赠精子出生的孩子。***妈想在他们完成学之后再告诉他们这个事实。
这三胞胎孩子蹒跚学步的时候,Emma就和她爸爸分开了,但在英国考文垂大学读书的时候他们又住在一起。有一次他们一起去划船,在船上他对Emma说”我不是你的爸爸“,Emma是在诺丁汉的一个诊所接受捐赠精子而出生的,而他一直都是不育的。
船上的对话深深地打击了Emma。Emma回首过去,说,“那个男人在我们的生活中缺席多年,从三岁到十三岁,他几乎都忘记了我们的生日。我不会期待有一个真正的父亲。”Emma不久之后便搬出了她“父亲”的房子,便与***妈同姓,并通过法律途径将她爸爸的名字从出生证明中抹去。由于出生证明的不准确,法律接受了她的请求。
Emma不责怪***妈,***妈总是心甘情愿地回答她所有问题,且总是把孩子的利益放在首位。Emma也加入了接受捐赠登记机构,她希望能找到她的亲族。同时她坚信既然我们不能扭转捐赠的概念,那么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如何让后代生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