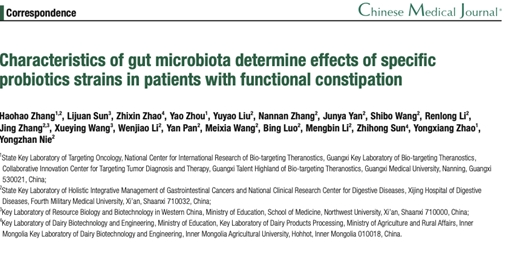不合理使用抗生素导致超级细菌的出现,使感染病已经面临无药可用的挑战。为此,中国开始史上最严厉的整治抗生素不合理使用乱象的行动。
抗生素资源总有一天会枯竭,我们将进入“后抗生素时代”―――世界重新面临没有抗生素的境遇,无药可用。
“现在可以说没有新药了,感染病已经面临无药可用的挑战。”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马小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未来10年,全新的抗菌药物不会超过3个,而且是在研发阶段,未必会上市,因为有可能会失败。
这就是细菌耐药性的结果―――由于不合理使用抗生素,加速了细菌耐药性的产生。
一些有害的细菌对原打算杀死它们的药物不断增加抵抗力,就是耐药性。
英国耐药性监测实验室主任利弗莫尔博士这样描述“后抗生素时代”―――其实情形很好想象,和抗生素出现以前相差无几:所有腹部手术将风险骤增,因为腹膜炎将难以控制;切除一根发炎的阑尾将变成性命攸关的大手术,因为细菌很可能会进入血液,引发危及生命的败血症。
2011年11月10日,卫生部医政司赵明钢副司长公开表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已经进入最终修订阶段。
今年4月,历届最严的一次抗生素专项治理整顿工作也在全国展开。一些硬指标已基本实现:三级综合医院抗生素的种类原则上不得超过50种,二级综合医院抗生素种类原则上不得超过35种,门诊患者抗生素使用率控制在20%以内,住院患者抗生素使用率要控制在60%以内。
尽管规范使用抗生素的脚步正在加快,但感染科医生专业队伍的建设缺失以及缺乏质量可靠的临床微生物的支撑团队,是不合理用药的重要基础性缺失。
合理使用抗菌药物,虽然不能遏制已经出现的耐药菌,但可以延缓和减少耐药性的出现,也为开发新药留出时间。
超级细菌魅影
2008年,任何一种抗生素都无法杀死从一名瑞典病人身上采集的肺炎克雷伯杆菌。更可怕的是,使肺炎克雷伯杆菌具备这种强大能力的基因可以轻易在不同细菌间传播。
早在2000年,纽约大学Tisch医院微生物实验室,就从一位接受重症特护的患者身上分离出肺炎克雷伯氏菌。
因为耐药菌越来越多,上世纪末,死于感染的人数上升至2000万人。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世界死于感染的人数每年为700万人。
2010年,欧洲有25000人死于抗药性细菌感染。
对于致病细菌,我们真的到了无药可用的地步?
“有时候的确是这样,就是泛耐药细菌的问题。实验室研究证实,泛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只对极个别抗生素有效,如多粘菌素B,但这种抗生素国内临床上没有。”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刘正印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在2009年,刘正印遇到了一名感染泛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患者。
这位21岁的女孩刚刚接受了肺移植,医生就在她的胸水和痰液中发现了高度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
“它能抵抗我们手头的几乎所有抗生素。泛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仅对多粘菌素敏感。而多粘菌素是一种很老的抗生素,由于对肾脏有严重的损伤,早已退出市场。”刘正印说,即便找到多粘菌素也无法使用,因为病人患有肾功能衰竭。
这名女孩13岁时,就被诊断出患有极易受到细菌感染的疾病―――肺部囊性纤维化。因此,在过去8年,她一直在使用各种抗生素。
大量抗生素的使用,使女孩的体内产生了多重耐药性细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超级细菌”。
刘正印说,泛耐药细菌几乎对所有的抗菌药物都耐药。这种细菌现在很多,而且几乎无药可治。泛耐药细菌最典型的就是鲍曼不动杆菌,以前都认为这种细菌不会致病,但是后来发现它是致病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超级耐药细菌,像NDM-1(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1)细菌。
NDM-1细菌,即2010年出现于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地区,又传至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欧美国家的“超级细菌”,已造成170余人死亡。
“这仅是产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NDM-1)的大肠杆菌而已。”刘正印说,其实在20世纪初,一些大的杂志的文章里就报道过很多超级耐药菌。如临床中出现的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叫MRSA、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的大肠杆菌等等,这些细菌的产生与使用抗生素都有一定的关系。
关于NDM-1菌的耐药性,刘正印解释:平常的大肠杆菌产生普通的β内酰胺酶,很少产生金属β内酰胺酶。此酶对抗生素中碳青霉烯系列的药物,如亚胺培南、美罗培南等产生耐药。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是抗菌药物的“航空母舰”,极其强效。这类药物被称为超广谱强效抗生素,是医生的“撒手锏”,专治各种难治性感染。
所谓超广谱是针对抗菌谱而言。一种抗生素只对一定种类的微生物有作用,即抗菌谱。
如青霉素,一般只对革兰氏阳性菌有抑制作用、多粘菌素只对革兰氏阴性菌有抑制作用,这类抗菌药物被称为窄谱抗生素。
氯霉素、四环素等对多种细菌及某些病毒都有抑制作用,称为广谱抗生素。
抗生素过去常被称为抗菌素,是指一种生物对另一种生物有抵抗作用。
编码NDM-1的基因还具有极强的传播性。这种基因被发现位于细菌体内的质粒上。质粒是游离于细菌染色体外的一个个能独立复制、自由交换的DNA环。耐药菌可以直接复制带有耐药基因的质粒,然后把质粒转移给不耐药的同伴。
如果没有质粒,细菌耐药性的扩散通常需要好几代才能完成。
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细菌群中便“让一部分菌先耐药起来,先耐药的菌带动后耐药的菌,最终达到共同耐药”。
最有可能诞生泛耐药细菌的地方,是抗生素使用最多的医院。
哈佛医学院的教授罗伯特·莫勒林博士指出,MRSA和肺炎克雷伯氏菌一样,最早也出现于特护病房中,特别是动过大手术的病人。
“这几年,泛耐药细菌在临床某些科室比较流行。”刘正印说。
有矛就有盾
1928年青霉素问世。这也是人类最早发现的抗生素。青霉素的使用使人类平均寿命出现第二次飞跃(第一次为牛痘),延长了20岁。
当时,人们都乐观地认为,从此以后人类面对细菌感染就不再无助。其发现者弗莱明爵士因此获得了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不过,他当时就科学地预见:青霉素耐药性的出现指日可待。
“他抓住了事物本质及发展变化规律:有矛就有盾。细菌的耐药性伴随着抗菌药物的问世一直在不断地演变。很难说,人类是否已经获得了胜利。”马小军说。
青霉素的临床使用是在1943年。
“当时的细菌都没见过世面,一支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就可以控制了。”刘正印说,从抗生素临床使用到现在已经快70年了,细菌的见识越来越广。这意味着细菌对抗菌药物的最低杀菌浓度在一点点增长,对药物的敏感性越来越差。
在抗生素的使用过程中,最低抑菌浓度随着用药的历史,水涨船高。
比如,以前最低抑菌浓度是0.01微克/毫升,现在已达到0.1微克/毫升,增加到了十倍,有的甚至增加到1微克/毫升。以前可能用40万单位、80万单位的青霉素,用一点,病人就好了。现在要增加到800万单位。
刘正印说,白求恩大夫当初被细菌感染,一支盘尼西林就可能救他的命;如果放到现在,多少盘尼西林可能都没用。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曾有文章称,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用青霉素治疗就行;到20世纪末,用效力更强的万古霉素治疗都已经不起作用。
在细菌和抗生素的对抗中,前者总是领先一步。
四环素类中,有一种叫替加环素的药最近刚上市。英文名叫TIGER。
这种药最初体外药敏证实,除了对铜绿假单胞菌无效,对其他都有效。
“它比碳青霉烯类抗菌谱更广,比如说泛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对它可能有部分疗效。但最近这几年国外也有耐药的报道了。”刘正印说。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除了抗生素,我们对抗细菌的手段可谓乏善可陈。而使用抗生素必然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
刘正印认为,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出现耐药性,这是避免不了的。病治好了由此产生耐药性,这是二重耐药菌感染,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不合理使用。
“即便是合理使用也会产生耐药性,不合理使用更会产生耐药性。如果既不合理使用又没有达到什么效果,又产生了这么多危害,是不允许的。”刘正印说。
马小军也认为,感染病人必须用药,但即便最规范地使用抗菌药物,细菌的耐药性也会出现,只不过出现的趋势能够慢一点。
最简单的生物也有趋利避害的本能。
在药物造成的生存压力下,细菌总有绝处逢生的抵抗力―――与真核生物相比,它们有较高的基因突变率、极快的繁殖速度以及可以轻松实现的基因互通有无。
以较为常见的致病菌肺炎链球菌为例,其对青霉素耐药的菌种于青霉素在临床使用24年后出现,其对红霉素耐药的菌种出现于红霉素发现后的15年。肺炎链球菌过去对青霉素、红霉素、磺胺等药品都很敏感,现在几乎“刀枪不入”。
对于较为年轻的氟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如环丙沙星、氧氟沙星),则是在其中的环丙沙星批准用于临床之后短短4年时间就出现了耐药。
不过马小军与刘正印都认为,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促使一些耐药的、变异的超级细菌加快产生。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国际范围内调查显示,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约30%,而中国住院患者中使用抗生素的占80%至9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或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占58%、门诊感冒患者有75%应用抗生素,大大超过了已经很不正常的国际平均水平。
抗生素不合理使用造成中国的细菌耐药性问题尤为突出,我国临床分离的一些细菌对某些药物的耐药性已居世界首位。
但马小军并不同意“中国是滥用抗菌药物最严重的国家”这一说法。
“因为‘滥用’的定义并不明确,到什么程度是滥用?是用滥了?还是泛滥了?是主观‘滥用’还是不明就里?因此,这么评价不是很科学,也有欠公允。”马小军说。
“像去年的超级细菌,它是从印度传到欧美,这肯定与抗菌药物使用得多有关。这也说明抗菌素的不规范使用是全球问题。”马小军认为,应该说目前抗菌药物是欠规范、不合理应用的多。
大型制药企业在抗生素研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一个原研药物制成新的抗生素,从筛选结构到初具模型再到临床应用需要十几亿美元,周期得4年到10年不等。
10年,这段空档期,对于耐药菌,人类要么无药可用,要么只好重新启用以前被淘汰的高毒性药物。
有人形象地比喻:最高端的抗生素原来是大炮,结果现在只具有气枪的功能了,可是细菌已经长成大象了。
这些开发出来的新抗生素,不像病人须终生依赖的糖尿病新药;也不比病人一用就是数个疗程的抗癌新药。抗生素的目的是治疗感染,因此处方只会限于数日到几星期。
而且,数十年研发出的新药,两三年内就会出现耐药菌。上亿研发经费损失严重。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大药厂已经悄然消减了抗生素的研发经费,有的甚至退出了这一领域。
“到现在为止,在中国,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抗生素没有几个,原研的抗生素我不知道有哪几个,大多是模仿的。”刘正印说,原研药物与仿制药物,在工艺、技术、效果等方面可能都有很大差异。
这就是为什么国外原研的抗生素到中国卖那么贵,中国仿制后价格便宜。
用闷棍还是用小棉棒
抗生素的使用要安全、有效,最后是价廉物美。这三点是药物治病最基本的原则。
目前,抗生素在应用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有医生、病人的责任,也有药企和社会的责任。
刘正印说,药企要盈利就要推销抗生素,推销的过程中就会采取不合理的手段;另外,医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再说患者,有很多患者家属来了说孩子发烧39度多,不管是不是细菌感染就要求用抗生素。而大部分感冒是病毒引起的。
刘正印认为,医疗管理部门在抗生素的应用方面也有一定责任。比如药价不合理,医生的工资低,病人知识没有普及到等等。
还有畜牧农业的问题。饲料里含有大量抗生素,动物在饲养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耐药性,通过食物链传播到人身上。即便是从来没用过抗生素的人体内也会出现耐药性。而这方面的监管几乎是空白。
“耐药宝宝”就是很好的例证。
广州市妇婴医院曾抢救过一名早产儿。使用头孢一代至四代无效,又改用顶级抗生素泰能、马斯平、复兴达也无效。细菌药敏检测显示,这名新生儿对7种抗生素均有耐药性。
专家推测新生儿耐药或来自母亲―――孕妇在吃大量抗生素残留的肉蛋禽时,很可能将这些抗生素摄入。
动物产品中残留抗生素,已经成为耐药菌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时至今日,在中国,超范围、无针对性地使用抗生素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查显示:我国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比例超过46%;而在加拿大和美国,过量使用抗生素的比例是15%和30%。在使用量、销售量列在前15位的药品中,抗生素占了10种。
“延缓细菌产生耐药性和减少细菌耐药性,这是我们合理应用抗生素最基本的。”刘正印说。
正常情况下,若是药物用的剂量不够,用的不合理,刺激细菌就会产生变异。细菌在药物选择性压力诱导下而产生变异,是细菌产生耐药最常见的机理,自然变异的很少。
诱导就是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用不好反而让它变异了。所以有时候本来是很简单的病人,由于不正规的治疗出现了耐药性。
“就像我们打闷棍,一棍子打下去,把脑袋打扁了,细菌就死了;如果拿小棉棒打下去,没打死把它打疼了,它就知道反抗了。”刘正印形象地比喻。
此外,多数病人在症状好转后,往往立刻停药。这样,耐药性的细菌就会逐渐积累,在遇到下一波抗生素攻击时,再获得另一种耐药性。
“所以,我们要求抗生素应用时,剂量与疗程要足,药效要好。”刘说。
“在该用的病人身上毫不犹豫地用,不该用的病人尽量不用。这样就可以尽量避免耐药性的过快产生。”马小军说。
但是如何合理应用,有时仅根据书本而没有明确的细菌培养是很难的。刘正印认为,对微生物实验室人员进行培训,让他(她)们掌握各种微生物的培养方法和技巧,提高培养的阳性率,为临床医生提供帮助非常重要。
因此,合理应用抗菌药物不能仅单靠临床的医生,如果没有微生物的结果,临床的医生就得凭自己的经验判断感染的部位、病原体、选择的药物等等。而不同医院、不同科室、不同级别的医生经验差异很大,即使同一个层次的医生经验也不同。
除了用药不当之外,在病房里也有互相感染的情况。
“我们医院要求勤洗手,而且要求按正确的步骤洗,这样就减少了细菌经医源性传播的可能性。”刘正印说。
加强家属的探视也是为了避免细菌由家属来传播,这也是抗生素合理应用的部分。避免细菌在病人之间的传播而产生耐药性感染,也是值得重视的。
政策层面的规范也在进行。8年前,中国已出台了关于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的相关办法。2004年7月1日起,抗生素再次被明确规定为处方用药。
据卫生部监测,协和医院是北京市抗生素使用率最低的医院。事实上协和医院早在1984年就出台了首个《北京协和医院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南》。
卫生部即将出台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将抗生素分为三大类,非限制类抗生素、限制类抗生素和特殊使用类抗生素。
“把抗生素分成三个级别使用在协和医院已经实行很多年了。协和医院将此作为绩效考核的标准之一,如果使用不合理医生会被扣奖金、找谈话。”刘正印说。
中国把传染科当成感染科
“如果根据‘滥用’的结论对整个抗感染领域进行评价并不适宜。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孩子犯了错误是因为他不知道,能说是他的错吗?”马小军的诘问并非没有道理。
“在中国一直把传染科当成感染科,真正感染科医生并不多,所以很多呼吸科和血液科的医生都成了感染科医生。”刘正印说,传染与感染其实差别很大。感染性疾病包括传染性疾病,后者仅是前者的子集。而专业的微生物检测人员就更少了。
造成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因素很多,马小军归结为:缺乏两个层面的重要的技术支撑。
首先,感染科医生的专业队伍的建设缺失,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多数医院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感染科的建制,现有的建制可以说是几乎形同虚设。这是大问题、深层次的问题。
大多数感染性疾病的诊治都是其他专业的医生负责的。而感染科在国外是个专业学科。
“现在已经是时候从高等医学教育的根基上,将医科大学的培训转型到感染性疾病的培训,因为它同时可以覆盖传染病。解放初期,由于感染性疾病高发,重视传染病是应该的,但是现在可以转了,也应该转型了。如果再不做的话,短期内还是不会有质的改变。”马小军说。
中国的医科大学到现在为止还着眼于传染性疾病的培训,而不是感染科的培训。我们有传染病教材、有微生物教材,但是没有感染性疾病的教材。
通常培养一个医学生需要5年,由医学生培养成一名成熟的专科医生至少需要10年。如果现在还不做,那么15年以后都不会有一个像样的感染性疾病专科队伍建设的局面。
“我们还能等15年吗?社会大众的健康需要还容许我们等15年吗?”
第二个技术支撑,就是我们缺乏像样的质量可靠的临床微生物的支撑团队。目前多数医院的微生物室是不赚钱的,单纯做微生物检测无法生存。不专业就无水准,这是常识。
微生物室在现行医疗体系的运营管理模式下,必须考虑自身的生存发展,以现在的物价体系以及各种指标评价,很多医院是不具备足够检测能力和资质来出具微生物诊断报告的。
有时候甚至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微生物部门人员觉得像什么菌就报什么菌,很可怕。技术力量的缺失是非常紧迫的。
马小军建议,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该考虑到实际需求,搭建一个平台,依托像北大医院、协和医院等大型三甲医院具有足够资质的微生物部门,让它的服务辐射到周边区域的医院。其他一些周边的医院就不要去考虑去建这种科室,有可能十年都不会遇到下一个少见的细菌让你鉴定。
“微生物检测的低水平重复是会造成巨大医疗资源浪费、会害人的。”马小军说。
如果能建立区域化的微生物诊断中心,可以保证多数微生物诊断能力不足的医疗机构重要的需求。既不需要浪费人力、物力等做没有质量控制和保障的病原学鉴定,也可以让能力足够好的医疗机构的微生物部门两性运转,发挥集约化的整体优势,为患者提供可信的检测报告,从而科学指导抗菌药物的应用。
抗菌药物的处方包括两个模式:经验用药和病原目标治疗。
经验用药,是第一剂抗菌药物处方时,医生并不知道是什么菌导致的感染,但为患者的治疗需要,应该开具的抗菌药物治疗。这个模式是最多的临床抗感染模式,依靠的就是第一个层面的技术支撑,即专业的感染科医生队伍的建设,因为它需要经验。
病原目标治疗,是第二个层面的技术支撑。有能力、有资质的微生物诊断部门或区域化的微生物诊断中心,刚好可以帮助医生做目标性治疗。
马小军说,这两点是解决目前不规范用药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实质性规范医生使用抗菌药物的行为。
对个人来说,只要勤洗手,就能大大降低感染几率。
“现在采取行动、管理抗菌药物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延缓耐药性的出现;由于细菌耐药性产生、传播机制较多,医疗机构还应同时做好医院感染控制工作,尽可能让感染不发生。这是未来我们必须要走好的一条路。”马小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