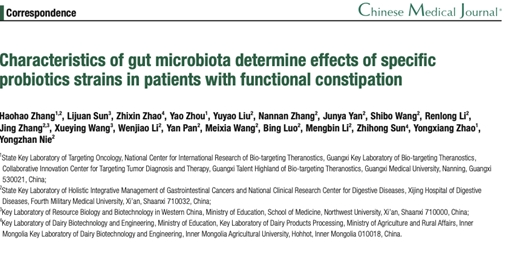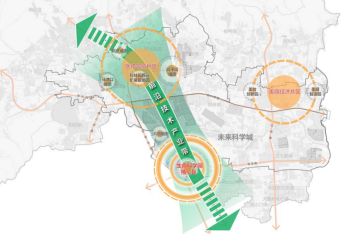在新药开发的过程中注意及时调整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关注的焦点,这将有助于科研人员更好地开展科研合作,以便更快地开发出新药产品。
基本上一直都处于停滞不前状态的新药获批数量与不断攀升的新药研发成本之间已经到了严重失衡的地步,大部分的新药研发成本都变成了沉没成本,这让我们不得不关注制药企业新药开发能力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也做了各方面的努力,这其中就包括在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方面的投入,尤其在可以将实验室研究成果转化成临床应用和新药的转化医学人才和基础建设方面下了大力气,美国设立的“临床及转化科学大奖(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Science Awards)”和英国建立的生物医药研究中心(Biomedical Research Centers)都属于这方面的工作。在他们的推动下,学术科研机构和制药企业之间也达成了不少的合作项目。不过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对全世界的知识产权“铁律”进行一番根本性的变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散布在各个国家的科研院所和制药公司里的科研人员与临床医生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取得更大的成果,开发出成功的新药产品。

大型制药公司一般都会包揽新药开发的所有工作,其中涵盖了从新药的初期研究、开发到新药审批和上市这所有的流程,不过采用这种垂直式新药开发策略的大型制药公司正在逐步的瓦解。最近披露的一份针对世界上19个最大规模制药公司开展的市场资本分析报告显示,这些公司在2005至2010年间的新药研发投入在10亿美元左右,可是他们同期的销售额却只有7500万美元,这个数字与之前8年的统计数据相比有明显的下滑,下滑幅度超过了70%。这种现象说明当前的新药开发模式是非常脆弱的,完全不能适应市场的些许变动,新闻媒体、电影、音乐以及运输行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那么有没有一种成本又低、效率又高的新药开发模式呢?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将各种各样的英才全都招致麾下,不论他们是来自新药开发、药物审批还是销售等行业,不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和地区,只要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就行。这种模块化(modular)的工作模式已经成功地在“抗疟新药开发组织(Medicines for Malaria Venture)”和“健康世界(One World Health)”等非营利机构中得到了实践的验证。
这些由政府、慈善资金、公司等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的组织表现出的这种利他行为(altruism)以及大量的知识产权交易机会和所谓的信用违约互换业务(credit default swaps,指的是一种保障业务,在新药开发工作中意指投资人给制药公司投资用于新药开发工作,可是如果制药公司的新药开发工作没能取得成功,那么投资人可以从制药公司那里得到一笔回报)都让坚固的知识产权壁垒开始松动,所以在新药开发工作中也开始不时地出现研究成果易手的事例,不一定要取得最终的研究成果,可以在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的时候就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出售给其他的机构和研究者。这种工作策略已经取得过多次成功,让抗疟疾新药、抗结核新药和抗查加斯氏病(Chagas disease,又名美洲锥虫病)新药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了临床试验。如果这种行之有效的“非营利式工作模式”也可以在经过某种“改良”之后移植到营利性质的制药企业里,那么一定会引得来自各行各业和世界各地的投资人蜂拥而至,因为这种模式一定会成功的。
如果要在制药行业里推行这种合作模式,那么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处置和知识产权相关的问题。脱离现实的预期以及过时的知识产权管理结构是当下限制学术科研单位与非公有企业之间合作最常见的问题。尽管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让一款配方变成一款药物产品,可是在制药领域里最主要的知识产权问题就是“配方问题(composition of matter)”。在这种知识产权管理模式下最紧要的就是新药研发阶段,各个研发机构也都把新药研发阶段的工作看管得最为严密,研究数据、试剂、配方、原理一概不许外泄,绝对不容许泄密的事件发生。
不过现在有人正在努力尝试打破这种局面,他们希望用不存在知识产权问题的科学常识和集思广益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莫过于Linux系统。现在,这种努力已经开始起作用了。在开展合作的企业和科研单位之间已经有交易开始进行,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改革,因为股东们还是非常关注知识产权问题。和非营利机构的利他行为不同,在营利性的经营活动中仅仅提供开展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条件还不足以吸引到合作伙伴。在采用垂直式研发模式的大型制药企业中关注配方问题是理所应当的,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分子是不是会变成一款成功的新药,所以除了研发人员之外,企业的每一位员工(股东)出于自身利益的角度也都会对新药的研究工作守口如瓶。不过在采用合作模式的企业中该如何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促成新药开发工作并且取得最终的胜利呢?
新药研发模式的转变。开放的合作模式,不断更新的知识产权以及根据模型设计的发展路线图,这一切都是帮助新药开发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缺一不可。
也许制药企业们可以从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等移动设备制造商那里取点经。移动设备制造商也长期受到知识产权问题的困扰,束缚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因为有很多厂家为某个概念或者想法(而不是某个配方)申请了专利,这个教训应该引起制药企业足够的重视。在移动设备制造领域有很多企业都持有专利,比如语音识别技术专利、触屏技术专利等,但是最主要的专利还是存在于我们消费者最终购买的产品当中,也就是说这个最终产品的制造商才拥有最重要的知识产权。
如果将这一套照搬到制药产业当中,那么最主要的知识产权就应该从最开始的新药研发工作转移到新药审批工作当中,详见附图。接下来就让我们以HIV疫苗或降脂新药的开发工作为例进行简要的说明。在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下从事新药开发工作首先就得进行通盘考虑,提前考虑到今后在从新药研发到最终上市这整个流程的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然后将各种资源分别在每一个阶段进行最优的配置,这才能保证整个新药研发工作的成功。比如在开发HIV疫苗的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应该出现在整个工作流程的初期,只有前期的基础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才有可能在疫苗研究工作中取得突破,所以应该将更多的资源倾斜给前期的基础研究工作。
可是对于开发降脂新药的工作来说,最主要的障碍应该集中在整个新药开发流程的后半部分,比如搜集足够的数据资料判断这款新药最适于哪些人群使用,可以起到最好的降脂效果等,也就是说对于降脂新药的开发工作来说设计III期临床试验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应该将大部分资源投入到临床研究工作当中。不过不论属于上述的哪一种情况,所有工作人员齐心协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资源配置工作中一定要贯彻Bayesian法则(Bayesian fashion,即必须取得所有参与者的赞成和支持),直至新药最终获批上市。
如果在新药获批上市之后还需要对新药开展更进一步的研究,那么还得为这些后续工作提供一套附加价值。如果可以不断地为新药发现新的适用人群,那么就能够不断地提供附加价值。其实这套新药开发模式并不新鲜,系统生物学的方法早就被广泛应用于选择药物作用靶点的工作当中,药代动力学模型(pharmacokinetic modeling)和药效学模型(pharmacodynamic modeling)也被用于确定用药剂量的工作当中,在估算新药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时当然也少不了药物经济学的身影,新药开发工作其实已经是一个必须依靠多部门合作才能完成的整体工作了。
当前被广泛采用的新药开发模式其实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工作方式。根本性的解决办法还得来自残酷的现实危机,而不是对未来的憧憬。这一点对于制药行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前的知识产权管理模式严重地限制和阻碍了制药企业与学术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所以必须做出根本性的改革。让新药开发工作遵循的传统的垂直式的工作模式改变成模块化的、多领域合作参与式的工作模式。